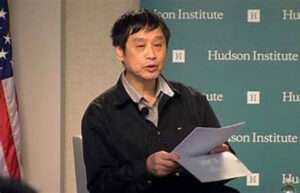《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是一部把“自我文献”写到刀口上的回忆录。它接续《蓦然回首》,把个人史从1976年一直写到2014年,把“文革之后的日子”与“当下的非常生活”连成一条线。读这本书,你会很快意识到:作者并不想把自己写成传奇,他更像一个认真做笔记的人,把关键的人、事、时、地、因果一一记清楚,留给后来人判断。这种写法,看似平实,实际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叙述选择——它把回忆从姿态里抽出来,放回到可核对、可互证的生活细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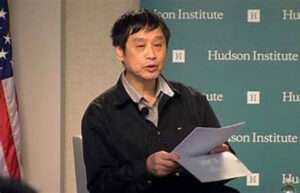
不先交代作者的背景,很难理解这本书的语气为什么这么克制。徐友渔本是学院派学者,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读研、任教,赴英国牛津大学跟随达米特学习,回国后破格晋升。他横跨数学训练与分析哲学,习惯用清楚的概念、干净的论证说话。《革后余生》延续了这种理性气质:从恢复高考、考研、出国,到回国后把学术转向公共议题,再到2014年因纪念“六四”被以“寻衅滋事”刑拘,最后取保候审,每一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朋友胡平的长文回忆,等于是给这本书加了一张人物关系图:两人同城相识、通信切磋、互相鼓励报考、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彼此扶持。这些第三方的细节,给了读者一个重要的参照:书中讲的人和事,并非孤立的“自说自话”,而是有相当广的目击者与见证链条。
把这本书放在徐贲所说“自我文献”的框架里看,更能读出它的野心与节制。“自我文献”不是自我抒情,而是把一个人在特定历史与制度压力下的感受、思考、选择,用第一人称原样记录下来。它往往带着选择性记忆、审查与自审查的痕迹,也留下许多“空白与沉默”。好的“自我文献”,不是靠把“我”放大来动人,而是借由可触的日常,让读者看到制度如何穿过衣食住行,改变一个人的反应方式。《革后余生》正是如此:它既不把“文革”当作纯回忆的终点,也不把“今天”写成抽象概念,而是用一个哲学家的亲历,把二者缝合成“极权条件下的日常”。
先看内容线索。全书大致有三条交叉的路:学术之路、公共选择之路、看守所之路。学术之路写得并不炫技:恢复高考后上大学、二年后考研、赴牛津、回国任教、以《“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些节点快速交代,重点不在列“战功”,而在说明他的理论偏好——要把问题讲明白,不爱大词。《革后余生》真正花力气的,是“从书斋走向公共”的过程。作者写他如何参与1989年前后的联署与对话,如何在“六四”后把研究兴趣从语言分析转向政治哲学,如何与体制内外朋友共同发起《零八宪章》相关倡议,如何在刘晓波案、诺奖事件上承担公开连带的风险。胡平的回忆补上了很多具体场景:拒绝撤回签名、不给警察“吃项目餐”、面对笔录坚决“不看不签”。这些细节解释了为什么2014年的那场“私人住宅内的纪念会”,会被当局视为“拔旗”行动的目标——作者不仅有专业声望,更是体制内外沟通的连接点。
第三条路,是本书叙述最强的一部分——看守所生活。那间二十来平米的监室,塞进十七个男人,其中多人是重罪嫌疑;“牢头”开口问话的气势、同囚们听到“因纪念六四被抓”后态度的骤变、众人改口称“徐老师”“徐老”的礼数……这些具体、准确、有温度的细节,让读者感到一种强烈的现实触感。更关键的是,作者在看守所里继续做“哲学”:每次提审都把问题追到概念根上——“什么叫寻衅滋事?与我们的行动如何相关?”当对方以其他罪名威胁,他则指出“定性任意”的逻辑后果;当被要求“写一个认识”,他就以“形势判断失误、主观无恶意”的表述,既不出卖他人,也不自污,把“认识”写成一份可公开的历史文件。这些处理不是斗狠,而是把“规则意识”搬进审讯室,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在跟一个散兵作对”。这份镇定,来自他对“记述者角色”的自觉:保留事实细节,保留推理脉络,保留可以互证的证词。最后,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他,他将全部奖金捐给“天安门母亲”。这不是姿态,而是把叙述与公共行动缝在一起。
从叙述、语言与结构看,这本书有三点很值得非虚构写作者借鉴。其一,叙述的“低姿态”。作者不铺排史论,不用“情绪大词”,而是用一连串“可核对的事实”搭起骨架:时间点、地点、人物、说过的话、发生的动作。这种“低姿态”,恰好给了读者最高的信任。其二,语言的“分析性”。即便是在被羁押、被威吓的场景里,作者仍尽量把句子写短、把概念说清。比如“我不看,也不签名”的拒绝,前头是对“笔录可能被剪裁”的推理,后头是对“敢作敢当”边界的划线——这不是爽文式的反怼,而是把理据摆在对方面前。其三,结构上的“互证”。书里多处让第三人叙述与自述交叉出现:友人的回忆、同行的见证、公开的奖惩与通告,它们与作者自述相互“搭扣”。这使文本在“自传”与“证言”之间找到了一种稳固的中间态——既保留第一人称的温度,又不过分依赖“我”的说服力。
把它和“文革前后、文革后30年”的回忆写作相比,最大的突破在于时间线的“延长”与问题意识的“转向”。不少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录以“文革反思”为核心,叙述往往止于个人的忏悔与赎罪,或者止于“从荒谬返回正常”。《革后余生》没有把故事停在“赎罪与回归”,而是把“后革命”的日常写成“持续的非常”——制度对日常的渗透并未消退,个人在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调适并未结束,“不正常生活”的常态化反而成了需要被记载的新“历史”。再与作者自己的《蓦然回首》相比,前者更多是“生成史”:少年、青年的思想与选择如何一步步定型;新作则是“检验史”:当这些选择真正要承担成本时,一个人如何在具体制度里站稳。两本书合在一起,才构成胡平所说“完整的自传”——从立志、成学到担责、受难、再回望。
“自我文献”的意义,在这部书里被做得很具体。徐贲提醒我们:研究此类文本,要特别留意选择性记忆、沉默与自我保护机制,也要做互文比对、语境分析与道德反思。《革后余生》有意识地预先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工作——它尽可能减少“不可考”的段落,多写“可求证”的事实;它不靠“高声谴责”建立道德,而是通过一连串“承担责任”的小动作,让读者自行判断公义的位置;它把“非常时刻”的记录落在“日常细节”上:不陪警吃公费饭、与审讯者对视、在监室里被称呼“徐老”——所有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动作,加在一起,恰恰构成二十一世纪极权条件下的“日常生活”切片。这里的“日常”,不是家常里短的隐逸,而是时刻被国家权力穿透的日常:一个人怎样说话、怎样拒绝、怎样签名或不签名、怎样承担,全部与风险绑定。记录它们,本身就是对“把公共问题降格为私事”的反抗。
从写作技法上,这本书还给中文非虚构类历史回忆提供了几条可操作的借鉴。第一,“写可验证的细节”。哪一天、在哪儿、谁在场、谁说了什么、怎么回应的,尽量完整。这样,回忆不仅是“我说”,也是“可查”。第二,“把叙述与论证分开”。该讲事实就讲事实,到了需要判断时,把判断依据摊开来说,让读者知道你是怎么想通这一步的。第三,“保留他者的声音”。让同案或友人“入镜”,既增加可信度,也避免自传的自我封闭。第四,“不追求‘完美的我’”。这本书没有给自己涂金,反而多次承认“形势判断失误”“主观无恶意”之类的有限表达。诚实的边界感,比漂亮的豪言更能在历史里站住。第五,“从日常入手”。写制度,不必总是站在宏大叙事上挥刀;从盒饭、笔录、称呼、走廊里的脚步声写起,反而能让读者看见权力如何通过细节进入身体。
与上世纪关于纳粹与斯大林体制的“自我文献”相比,《革后余生》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揭示了多么“新”的暴力形式,而在于它把“当代技术—治理环境中的软暴力”写出了质感。你很少看到血腥的场面,更多的是“流程化的折磨”:无止境的问询、标签化的罪名、程序性的威吓、让你自证其罪的笔录。这是一种把“异常”处理成“正常”的机制。写下它,既是证言,也是“防遗忘的教程”。它告诉后来人:当你在一个看似文明的制度里被要求“补一份认识”“签一个名字”“吃一顿他们买单的饭”,你该如何保持清醒、如何留下文字。
对中文读者来说,这部书的最大价值,也许恰恰在它的“不过度”。它不给你现成的口号,不用愤怒替代思考;它把一个人的一连串决定、犹豫、承担、拒绝,平平实实摆在你面前。你会看到一个受过严格逻辑训练的学者,在制度夹缝中一点点“做自己能做的事”:与体制内外结盟,把专业信誉押在公共立场上;每一次与警察打交道,都争取在规则之内占住理;进了看守所,仍然把对话变成“概念澄清”。这不是“把生命献祭给历史”的浪漫,它更像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对”的固执。这种固执,正是“自我文献”的可靠之处。
概言之,《革后余生》讲的是一个人如何把“读书人的本事”变成“公民的能力”。徐友渔用《革后余生》表明:写回忆不是为了自我抚慰,而是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盏小灯。也许灯光不够亮,但它照得见门槛、楼梯与陷阱;也许灯光会被风吹灭,但在灯火被吹灭之前,它启示我们:什么叫“正常的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仍要为之据理力争。把这盏灯递下去,便是这本书最大的写作伦理与公共意义。对于正打算书写自身时代的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清晰、可学的范式:用可验证的日常细节,去抵抗“不正常生活”的正常化;用克制与诚实,去建立记忆的可信度;用第一人称的见闻,去补足公共史料的空白。读完它,你或许会更愿意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哪怕只是几行日期、几句问答、一次拒绝的理由。在一个把沉默当成合格表态的时代,把话说出来,说清楚,就是难得的勇气。把回忆写成证言,把真实的“自我文献” 写成未来的“历史文献”,就有永恒的价值。
写作参考:
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一一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徐贲: 极权下的自我文献及其解读—《極權下的日常生活:見證者的回憶與記錄》導讀
徐贲:極權下的日常生活:見證者的回憶與記錄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