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崔卫平译文集《平行城邦》序,作者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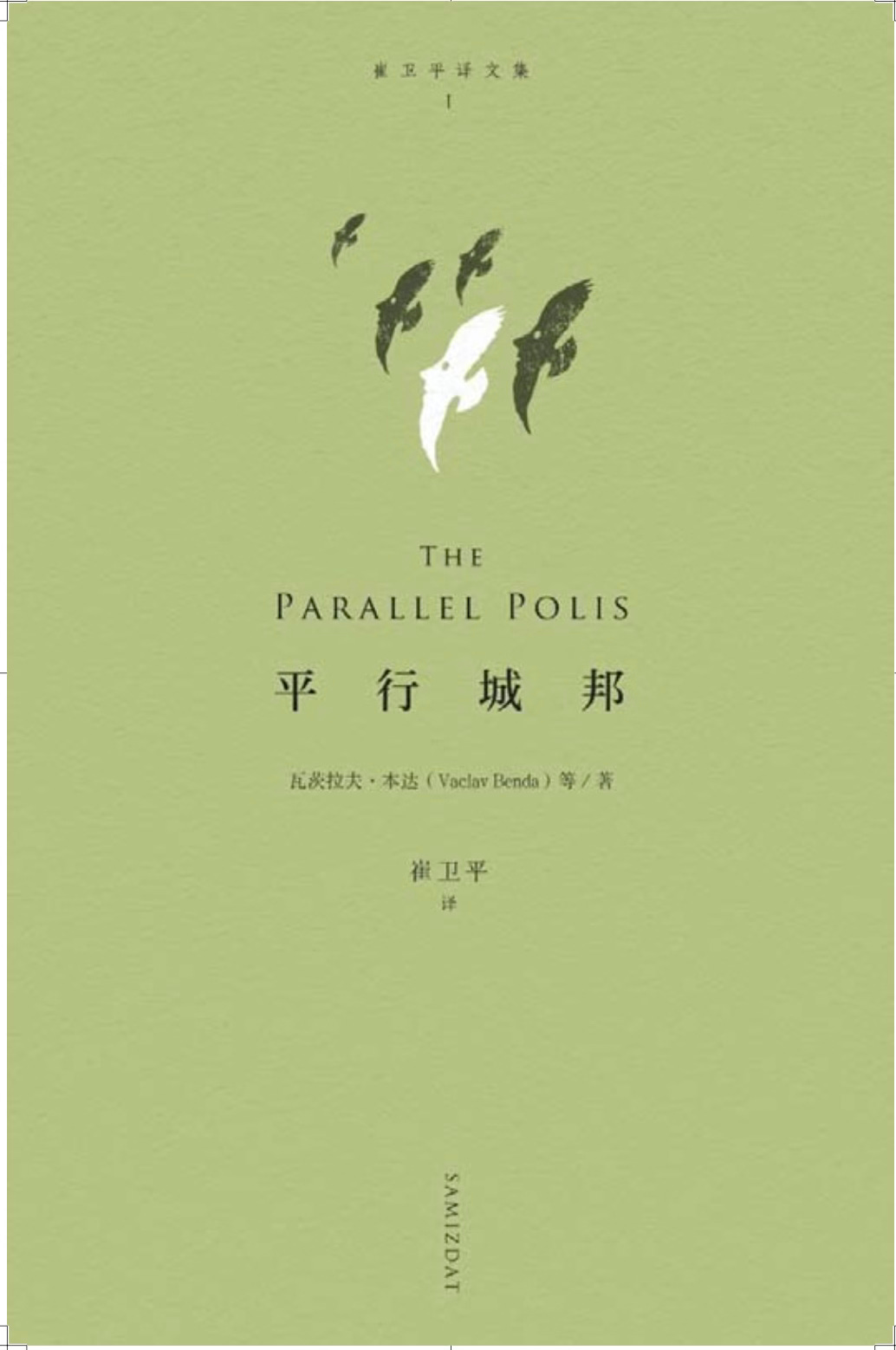
2017年2月8日,《纽约客》发表印度政治评论家和小说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文章《瓦茨拉夫·哈维尔关于如何创建一个 “平行城邦 “的经验》1,其中将哈维尔视为当今世界反抗极权主义的思想资源。米什拉的这个看法超越了许多人——当年作为持异见者的哈维尔,远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世界“遥远的怜悯和同情的对象”;哈维尔所批判的极权主义不仅限于共产政权,而且将西方世界的弊病也囊括在内。在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匿名统治、技术操纵及人工语言所构成的西方社会里,虽然在物质上更加成功,但是人们仍然感到深刻的无力感,感到自身真实人性受到压制,消费主义并不鼓励人们的责任感。的确,在米拉什提到的哈维尔写于1984年的文章《政治与良心》中,哈维尔把极权主义视为某种全球性现象,认为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极权主义政权并不仅是来自危险的邻国,不是什么世界进步的先驱,正好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危机的‘先驱’。”2
2016年川普的当选看上去坐实了哈维尔三十年前的警告。一个如此不靠谱的家伙被推到了前台,而太多人们仿佛不在乎真相,对基本事实缺乏兴趣,令另外一部分人们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力。川普在台上至少有四年,怎么办?米什拉想到了在他看来是哈维尔推荐的方案: “建立一个 ‘知情的、非官僚的、动态的和开放的社区,构成’平行城邦’”。不同于压迫性政权和谎言社会,在这样一个民间组织起来的地方,人们得以恢复“信任、开放、责任、团结和爱。” 米什拉认为哈维尔从中看到了某种“救赎的可能性”。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提到不久前在美国拉开帷幕的反川普运动,与哈维尔当年从事的公民活动有所匹配,这些自由世界的反对派,可以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平行城邦“中找到“避难所”,从而“在自由世界塑造一种救赎性的异见政治” 。
2019年1月,澳大利亚邦德大学高级助教丹尼尔·布伦南 (Daniel Brennan )发表文章——《在川普的年代读哈维尔》3,对于对米什拉文章中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位布伦南2016年出版过《哈维尔政治思想的意义》一书,是年轻的哈维尔专家,对哈维尔思想的认识颇具穿透性。针对米什拉有关“救赎”的思路,布伦南指出,哈维尔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没有提出或推荐一种“救世”的方案,他始终对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结构采取犹疑的态度,对于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路保持终生警惕,哈维尔天生是反乌托邦和反弥赛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的极权主义的分析才同时适用于共产政权和西方世界,如果说,乌托邦思想或弥赛亚情结所具有的终极/单极意向,也意味着一种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革命/暴力想象,那么哈维尔与这种暴力想象无缘。
在表达对于救世主的期待十分渺茫的同时,哈维尔关心什么?布伦南的这些分析都是很到位的:他感兴趣的是分析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如何说服个人采取违背自己道德直觉的行为,倡导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反思和个人责任,即每个人需要问自己,他们的行为对于有害的社会状况的产生或维持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哈维尔并非想要一个与权力相平行的异见地下社会,而是倡导人们“在阳光下改变个人行为”。这些都是抓住了哈维尔思想的根本。难能可贵的是,布伦南对于哈维尔这个人的气质把握十分准确,他举了一些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哈维尔如何经常谈到自己的缺陷,他这一辈子太多的自嘲只会在人们心目中贬低自己的形象,而这些恰恰是哈维尔所需要的——反对对于人类行为的英雄式解释处于哈维尔思想的核心,通过展示其自己的缺点乃至脆弱,可以达到对于社会现实及人们自身人性复杂性的揭示,这种复杂性才是今天政治和政治活动的基础。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也决定了今天反抗的条件——如果不存在或无法依赖一种英雄的伟大姿态或者殉道的政治变革,那么人们该怎么做?
布伦南是从米拉什的话题引申出去,并没有专注于“平行城邦”的问题。关于这个议题,布伦南仅仅说了一句“哈维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想法,但最终拒绝了这一想法,声称不要逃避任何政治现实”。在这个上下文中,似乎潜藏着一种理解,“平行城邦” 有可能脱离当下现实?这是什么意思?它符合哈维尔的原意吗?或者说,围绕着“ 平行城邦”,是否有过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那么,这个“平行城邦”也不是如同人们一望即知的含义?本文拟将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人不同意布伦南文章中的这句“哈维尔倡导的是个人责任,而不是集体组织的对政权的抵抗”。他把事情说得有点绝对了。2009年3月份,学者徐友渔、律师莫少平与我本人在布拉格与哈维尔见面时,哈维尔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零八宪章》之后的处境,我介绍自己说一连写了5篇文章,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山鲁佐德,不停地给吃人怪物讲故事,以免马上被吃掉,哈维尔沉吟了一下,答道:“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其中后半句的措辞是通过翻译及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哈维尔想要纠正我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
“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瓦茨拉夫·本达(Václav Benda,1946——1999)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介绍本达之前,我想先提到另外一个人——哲学家拉迪斯拉夫·海达内克(Ladislav Hejdánek1927——2020),在我的阅读中,海达内克是第一个使用“城邦”(Polis)这个概念并运用这条思路的人,他试图发展《七七宪章》的另一些面向。哈维尔1986年接受卡雷尔·赫维扎拉的长篇访谈4中曾经提到过这位海达内克,说是1976年秋天官方审判地下音乐人之后,为了保存庭审抗议所积聚的能量,人们打算弄一个平台或宣言,为此哈维尔前往拜访了海达内克,对方提醒这份将诞生的宣言“可以以不久前颁布的人权条约为基础”。51968年海达内克曾在帕托切克的推荐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所短期任职,与许多反对入侵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很快被革职,此时是一名锅炉工并在家庭大学教授哲学。
海达内克是《七七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和第二任发言人之一。他从1977年2月(《七七宪章》发布不久)到这年9月,给一位始终没有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写了21封信。这位在校的年轻人想通过年长哲学家加入“宪章”,但是被海达内克拒绝了。哲学家的理由是学习更重要。半年多的密集通信中,海达内克以平等的身份向年轻人介绍了“七七宪章”的意义、理论和实践以及宪章内部的讨论(流亡、忠诚与背叛)等,包括“宪章”无意招兵买马,并不致力于通过扩充人数来壮大自己。在第六封信中(署期为1977年3月19日),哲学家先是解释了自己没有及时回复的原因是警方为阻止他参加帕托切克的葬礼而提前将他弄到一个地方关押了两天,接下来海达内克引进了“社区”这个词,并说“社区的希腊语是polis”。6海达内克区分了“广义的政治”和“狭义的政治”,“社区”和“城邦”则属于广义的政治范围,在这里即使一个非政治的人所做的事情也具有政治意义,比如一个人从事某种研究、写作或艺术创作的方式,都在为他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做出贡献。鉴于共产政权的经验,海达内克反对过度政治化,但是他不同意抹去政治。他说:“没有政治或非政治是某种类型的政治,如果它成为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就会成为一种非常有害和危险的类型。”7
海达内克说得比较含蓄,但若是结合后来本达在“城邦”问题上的发挥,可以视海达内克想部分修订他的老师扬·帕托切克(Jan Patocka,1909——1977)强调《七七宪章》主要是一个道德行为而不是政治活动8的观点。1977年月1月8日,在《七七宪章》公布及哈维尔一行人被捕之后的两天,“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的帕托切克写了《七七宪章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文章,奠定了宪章的道德基础。两个月之后帕托切克的突然去世,更是给宪章抹上一道殉道色彩。海达内克开拓了社区/ 城邦的面向,其意义在于:道德关乎个人,成就在个人,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属于垂直方向上的;“城邦”关乎与你一道生活的人,福祉在他人和社会,属于与他人共在的水平方向上。
本达的这篇《平行城邦》(“The Parallel Polis”)发表于1978年6月下旬的《宪章通讯》上面,这份samizdat刊物我们下面还会谈到它。本达1946年生,1970年获查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校园生活的最后两年正值“布拉格之春”。他组建和领导了第一个独立学生协会,并活跃于一个天主教青年团体。1970年因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曾被起诉。1976年他也参加了声援地下音乐人的活动。但他并不是《七七宪章》第一批签署者,因为他在布拉格市中心广场附近的公寓是一个经常聚会的场所,暂时还没有遭到破坏。1977年1月中旬,针对签名者的迫害铺天盖地而来,他立即签下自己的名字。
本达称这是一篇“急就章”的文章,起因于他要参加一次《七七宪章》“智囊团”的小型会议,与会要求里有提供一份书面发言报告,到现场时本达发现只有自己这样做了。本达回忆这次会议召开时,《七七宪章》正处于某次危机之中。自“宪章”诞生一年半以来,这种危机经常发生,除了帕托切克的去世,还有签署者的再三被捕及流亡等。在本达看来,危机源自“宪章”本身——说实在的官方也仅仅是拿法律当挡箭牌,包括它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而“宪章派”却假装相信连官方都不相信的东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当然,通过自身的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宪章派至少暂时弥合了某种分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实际上,最初签署宪章的行为带来的欣喜若狂的解放感,逐渐让位于幻灭感和深深的怀疑,一种几乎是自杀性的道德冲动,并不能唤起更多普通人的支持。
本达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把在海达内克那里已经出现过的“城邦”朝前推进了,他以“平行城邦”作为自己这篇文章的标题。希腊语的“Polis”这个词,强调有着自身起点的公民与他人的关联,以及有主体身份的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所谓“平行”,即平行于官方主导的权力及社会机构。这个视野所埋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指望能够改变官方的现有权力及其掌握的社会机构,但是可以在它之外创造出另外一些必须的社会功能,与之相平行,用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本达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缓慢而坚定地创建平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s),这些结构至少在有限程度上能够补充现有结构中缺少的普遍有益和必要的功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现有结构,使其人性化。”9
本达迅速地用“平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s)来阐释“平行城邦”,觉得这两个字之间是可以替换的,在文章的主体行文中也是如此。更多出现的、起主导作用的是“平行结构”这个词。这更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平行城邦”这个词的含义,即也可以理解为“平行的社会结构”或“平行社会”。
本达列举了着眼于“平行结构”可以拓展的范围,包括:法律、文化、教育、学术、信息网络、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宗教。其中“文化”、“教育”和“信息”最容易理解,它们事实上已经存在,地下音乐的发言人伊万·希罗斯(Ivan Jirous,1944——2011)已经用“第二文化”为此命名。希罗斯并辨析了共产政权下的“第二文化”与西方不同之处:在西方,“第二文化”有可能被第一文化收买和吞噬即商业化,而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环境里,“第二文化“将独立于任何官方交流渠道及社会认可的价值等级。希罗斯在1976年9月对“地下音乐人”的审判中被判18个月的刑期。本达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服刑。本达继承了他的概念,称“第二文化是最发达和最有活力的平行结构。它应该成为其他领域的典范”,比如Samizdat、地下音乐、家庭大学等都是。
同样,经济领域中也已经出现平行结构的现象。有意思的是,本达把系统性盗窃、腐败和贿赂这些灰色经济也算在内,当然他不是提倡这些东西,而是说要建立严格的、符合道德的经济保障结构,“我们的社区应该建立在一个相互保证的系统之上,这种保证既是道德的,也是物质的”。至于“平行政治”、“外交”和“宗教”领域,目前主要还是处在展望阶段,此前有改革的共产党人及流亡海外者也表达过“平行外交”的想法,他们主要是想向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求助,试图运用各国共产党及其联盟的力量给苏联和本国统治者施压。
然而说到底,这些平行结构到底是抛开现有权力的机构从头起家呢,还是利用现有结构将其改造,多少还有些含混。最为含混的是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法律领域。显然,一个国家不可能有第二个法律系统,无法脱离现有法律结构。那么,如何从事平行的法律活动呢?本达解释道,目前的这个法律体系本质上被运用于宣传,因而有许多模糊的成分。需要利用这种特色,不断测试其被允许的限度,从而将从 “凡是没有明确允许的就是禁止的 “,过渡到 “凡是没有明确禁止的就是允许的 “。这么说,还是在现有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活动。这难道不正是《七七宪章》在做的事情吗?运用现有法律,将侵犯人权的现实纳入法制轨道之中。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本达用了“ghetto”这个词,它包含了少数人的“聚集区”、“贫民窟”、“与世隔离”、“封闭”等多重含义,本达的用意很清楚:他希望《七七宪章》能够有一个超越个人道德、牺牲及少数人俱乐部的视野,从自身走出来,拥有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结尾处本达写道:“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消除普遍的徒劳和无望的感觉,而不是助长这种感觉,我们必须努力从我们与该政权进行对话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可以说,本达的智慧在于阐述了一种后帕托切克的异议观点,这种观点将重心从个人道德及牺牲,转移到共同体的生活及社会结构。的确,反对活动所追求的,不应仅仅是牺牲在自己的活动之中,而是能够生活于自身活动之中,尤其是着眼于自身活动所带来社会的收获和社会的赢面,说到底是让社会赢、成全社会而不是成全个人。
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写于同年(1978)晚些时候。在这篇长文中,哈维尔对于本达“平行城邦”给与了热烈的支持,特地辟出一个小节来讨论这个话题,称本达所称发展“平行结构”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阶段”。10 哈维尔也是交替使用“平行城邦”和“平行结构”这两个概念,同时也运用“独立的社会生活”( independent life of society)和“社会的自我组织” (social self-organization)来称呼它们。然而哈维尔仍然强调它们的“非政治”性质,指出其“原本起源于政治之前的领域。……并非先验地产生于革新制度的理论当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真实的人们、真实的需要”。11 此时的哈维尔,仿佛对于“政治”有着某种避而远之的洁癖。然而,仔细阅读哈维尔的行文,他也并非仅仅强调个人道德及牺牲,而同样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着眼于个人在“城邦”(Polis)生活中的角色、意义,他提倡人们“生活在城邦生活的真实中”,对于城邦生活承担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哈维尔又进一步指出,意识到平行城邦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主流社会,撤回到一个隔绝的和封闭的状态(a retreat into a ghetto and an act of isolation)。如果说平行城邦造成一个小社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与大社会脱钩。实际上这种脱钩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会在这里或哪里与官方结构发生关系,正像哈维尔所举例的,人们总要在国营商店购物、使用官方货币和遵守官方的法律。他不无讥讽地说道:“人们自然可以在基层的平行城邦过一种有声有色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如果刻意为之,以此作为一个专项,那岂不是另一个版本的精神分裂的生活在谎言中?”12 哈维尔还提到了西方青年到印度寺庙遁入空门,认为这是逃避社会责任的做法。
如此说来,前面提到澳大利亚哈维尔学者布伦南称哈维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想法,但最终拒绝了这一想法”不完全准确。哈维尔当然提倡“平行城邦”即独立的社会生活;他只是不想让这个东西变成重新脱离现实的小乌托邦。当他言及一个不受官方污染的纯洁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以及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如何回避了社会责任,的确也不是印度米什拉所关注的救赎问题。
本达后来说他从未想过自己这么一个急就章的提法,引起多年争议不断。下面我将提供围绕着这个议题争议的一个片段,就近观看由此而产生的生长变化。因为语境不同,讨论的概念略有变化,但仍然指向同样的问题。
1986年到1987年间,加拿大历史学家斯基林(H.Gordon Skilling)为了写作他的《Samzdat和中东欧的独立社会》一书(1989),以“独立社会”的名义,向多位捷克斯洛伐克异见者发起了问询,一份问卷四个问题:
I. 你认为 “独立社会“一词在贵国目前的条件下是否具有相关性和意义?
2、如果是的话,你认为 “独立社会 “的基本特征包括哪些?
3、如此构想独立活动和组织其直接目标是什么?
4、 这样一个独立社会的长期影响和可能结果是什么?13
斯基林先是将其中七人的回复发表在美国《社会研究》杂志上面(1988),其中有希罗斯、本达、哈维尔、拉迪斯拉夫·海达内克和伊日·迪恩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1937——2011))等人,取标题为《平行城邦或中东欧的独立社会:一项调查》(“Parallel Polis, or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Inquiry”)。这个标题中,斯基林用“或”(or)隔开“平行城邦”和“独立社会”,继承了本达最早的用法,并用西方人相对容易理解的“独立社会”来与之匹配。1991年,斯基林和资深捷克语翻译家保罗·威尔逊一道,出版了单行本《中欧的公民自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声音》,其中公布了18个人对这四个问题的回复,其中大多数是《七七宪章》签署者,还有几位天主教徒。本达1978年最早的“平行城邦”的文章也被再次收入书中。
时隔近十年之后,“第二文化”的创始人希罗斯对于“独立社会”这个概念反应最积极。希罗斯继续强调自发起点,称“建立一个独立的或替代的或平行的社区是唯一有尊严的解决方案,因为权力剥夺了那些不参与其中的人的尊严。”14希罗斯的立场,符合他作为先锋文化人的身份,拒绝所有组织或准组织活动。即使在西方,他也是会同样是那种孤傲脱俗、不修边幅的那种人。1978年希罗斯出狱之后也签署了《七七宪章》。
另一位佚名作者也认为 “独立社会”,是分析极权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因为在共产极权中,任何立足于人们自己身上的东西,都不被视为天然的、正常的和人类的,因此哪里有自发性、哪里就有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社会“它是政治的,不是因为它为自己寻求权力,而是因为它遏制了极权主义的权力。”15旨在追求自身真实生活和表达,并试图反抗社会空间的原子化瘫痪,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社会无疑值得高度肯定——它的确是被极权官方“挤”出来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面向上的努力有着广阔的前景。
在本达新写的文章中,他发现,自他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最初任何乐观的估计,本达进一步指出平行结构与个人生命的反抗不同,个人的反抗是一簇鲜花,生长在一个不经意地避开极权主义杀戮之风的地方,然而当这些风向改变时很容易被摧毁。而“平行结构”则是一条壕沟,它的存在取决于极权国家有计划地加以摧毁,但在时间和手段允许的条件下,只有一定数量的战壕可以被消灭。16
然而归根结底,本达与大多数这批答卷者一样,认为“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即不能停留于与官方之间的表面断裂和对立。尤其是考虑到完全脱钩不可能(哈维尔再次阐发了他的反乌托邦立场),更不能沾沾自喜、以自身作为衡量事情的尺度,包括不能把“独立社区”视为一个“受迫害社区”而陷入愤世嫉俗或自我怜悯。即使官方千方百计驱逐独立活动,但是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们不能继而认为自己恰恰是处在某个边缘,以小圈子的身份和口吻出现在公众面前。相反,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需要与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拥有更加宏大和长远的目标。正如海达内克所说:“自由和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每一次独立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接受更高的义务来证明其正当性。”17什么是这个更高的义务和更有价值的东西?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的回答,正好是互相补充的。
本达强调,“平行城邦”这个方案有其优先考虑的内容,这便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保存或更新——以及维护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所依赖的所有价值、制度和物质条件。”18着眼于民族共同体的前途,在本达看来,眼下“平行城邦”应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增长和更新,创造重新承担责任和同胞情感的纽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平行城邦”要为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提供政治燃料和雏形。在这个意义上,本达甚至不同意运用“地下”、“第二文化”、“独立文化”这样的概念,认为它们过分限于某些局部。1927年出生的心理学家雅罗斯拉夫·萨巴塔(Jaroslav Šabata),是1968年坦克苏军入侵之后第一批被重判的社会主义反对派(1971年获刑7年半),前后三次担任《七七宪章》发言人(1978,1981,1986),他甚至认为可以不用“独立社会”这个概念,但是需要有一种独立倡议和活动(the independent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与社会民主化再生的深层过程相呼应,并能够作为更新的、普遍民主的先导。19
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及开放社会,也被认为是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米兰·希梅奇卡(Milan Simecka,1930——1990)是来自斯洛伐克杰出的持异见者, 1976年他的长文《秩序的恢复》描绘了进入1970年代之后所谓“正常化”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官方通过巧妙操纵个人利益而不是直接暴力而实现新极权统治,被认为是与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相媲美的一部散文作品。“多元性”处于希梅奇卡表述的中心。他希望在独立活动中所树立的,正好是未来社会所期待的:“鼓励多元化的元素,提倡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宽容,反感和抵制意识形态思维和所有形式的暴力(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令这些品质在社会中牢固扎根。20”教育和历史学家拉迪姆·帕劳什(Radim Palouš,1924——2015)为1982年《七七宪章》发言人,他呼吁当今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和生命相互依存的时代,因此,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们也要有他“整体的和全球的”责任,对人类整体的存在包括地球及环境,抱有一种开放和对话的态度。
当本达最初提出“平行城邦”时,“公民社会”的概念在这个地区尚未普及。此处多位当事人答卷已是80年代后期,因此,不止一位问卷的回复者,熟练地运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然而,对于公民社会的运用与西方也有所区别。在西方,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共产极权国家,第一,国家不履行其自身职责;第二,国家压制自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独立)社会里所做的工作及收获,其意义便不限于一般所说的“社会”,不限于在社会领域中的工作及其意义,甚至也可以类比于在国家领域之内的工作及其意义。海达内克便指出,“社会要努力赢回其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社会将再次决定其国家将是什么样子”21。伊日·迪恩斯特比尔为1979年《七七宪章》发言人,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他说,当独立活动的人们寻求途径来实现被国家所忽视、压制的社会利益及需求时,“公民社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个国家”22。
独立活动中的价值观为更多人关注和提及。在一个价值失范的社会里,独立或平行社会是培养正直、团结和宽容的天然形式,尤其是独立活动所释放的价值观——真理、自由、公正、人类尊严、文化记忆,这些都是人类活动的普遍保证。伊娃·坎特尔科娃(Eva Kantilrkova,1930——)是记者和电影编剧,1985年的《七七宪章》发言人,她提倡独立或平行文化重在创造普遍的文化意识,提供什么是卓越作品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并不专门属于某一方(独立的或官方的)。她也反对把不同区域绝对化,她认为即使在国家电影厂或者小剧院,偶尔也会有某部优秀作品出现,但是由于在公共媒体上缺乏正当的批评讨论,社会公众便没有机会吸收和消化这部作品,于是它就会像深渊上空短暂停留之后,跌入价值垄断所造成的真空之中。
也有宗教背景的人士在做出他们的回复时,对于由希罗斯那样长头发的人所代表的独立文化表示怀疑乃至拒斥,认为它们代表了西方社会颓废放纵价值倾向而并不足取。显然,宗教人士的普遍性考虑来自基督教世界观。
彼得·皮塔特(Petr Pithart,1941——),多年为政治和历史方面的samizdat作家、宪章签署者,1990—1992年担任过捷克共和国总理。在他的回复中,涉及了对“独立社会”内部的批评。如果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官方与独立这两个领域就变得非常相似,同样是封闭的。比如就samizdat写作领域而言,有人把这种地下出版的形式本身即当作一种尺度,而不讲究质量和批评,结果可能出现许多业余的“书写狂热者”,然而不见有价值的作品。这样,samizdat便会失去其读者。当然,皮塔特提醒道,任何批评都不能沦为人身攻击,而对封闭或半封闭的区域,最容易滋生人身攻击的条件。在皮塔特看来,某些人从最初的道德神圣沦落为人身攻击,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这些行为“不自觉地助长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处的不道德状态”。23 换句话说,这些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以其缺乏道德的行为,也会重新跌入他们从中独立出来的原先那个社会。
哈维尔着力关注的是平行结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它们如何作为一个能量的积聚点和爆发点,引发整个社会的聚变。用他自己的特殊语言风格,哈维尔总是喜欢用“不确定”和潜在性“这样的表述。尽管从目前或表面上看起来,持异见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群体,但是在他/她们周围,存在着一个潜在影响的广大领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这种影响就变得清晰可见。哈维尔这样说道——
《宪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焦点,但这个焦点却不断地将独立辐射到其边界之外。很难说这种辐射正在和将要在被辐射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将诱发什么成熟或发酵(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催化剂的话),以及这种辐射将将对任何未来的社会运动有什么贡献。近年的波兰历史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KOR24及其活动家似乎不能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改变总体社会状况或影响它。然后突然间,当公众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时,KOR的工作几乎在一夜之间便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KOR的最初的分析和理念性工作,一千万人的团结运动是如何产生的。25
在哈维尔的头脑中,始终镌刻着一个“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时刻”。任何人都无法判断它什么时候到来,包括哈维尔本人也不做无谓的乐观估计,1989年1月份他还被捷共当局判了9个月监禁(5月份获释),这年9月份他在布拉格一家鱼餐馆回答记者时,说到希望变革来得快一点,但“我们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26。然而,几个月后的12月29日,哈维尔从这个“国家的敌人”一举转变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民主的前景和社会巨大的潜在能量就是摆在那里!
而当社会危机总爆发、旧秩序崩溃的时刻,需要有一些纽带将这个社会连接起来,让人们能够互相联系、互相看见,在混乱中找出方向、建立秩序和树立价值。实际地说,也需要一张各种花式、不同脉络结成的巨大的网络,把正在处于暂时混乱当中的社会托住,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之所以比较成功,能够为今后获得一个和平起点,是因为有比较发达的公民运动及公民团体。而罗马尼亚枪毙齐奥塞斯库的举动,一般被认为是1989年转型的一个反面典型,那也是一个最为缺乏公民活动的地方。
哈维尔所说的《七七宪章》对于整个社会的辐射作用,在现实中的确有了十分可观的体现。首先,“宪章”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起点和平台,在政权的一再摧残之下它始终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签名人数有限,最终也只有不到两千人(一般认为是1889名)但是基本格局始终不变:一直到天鹅绒革命之前,每年更换三位发言人,代表三个主要的反对派脉络:一位来自前共产党人,一位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另一位来自宗教人士。在第一个十年中,《77宪章》共发布了约340份文件,到1989年底,大约颁布了近600份文件。这些文件由相关专家拟定,最终发布时都有发言人的签名。最初几年主要集中在人权议题上面,涉及就业歧视、文化禁令、囚犯待遇等违反国际人权条约的情况。其后几年所涉及的话题更为宽泛,经济、物价上涨、教育、宗教、科学研究、和平呼吁、环境、滥用药物、知情权、立法改革、年轻人的住房等,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所关心的议题。这些文件影响如何?伊娃·坎特尔科娃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某地的生态学家决定将他们的一些批评材料交《七七宪章》发表,但当这一消息传出后,地方当局为了避免被宪章文件所披露,立即动手改善。据说当地一位高级官员对于上级部门的愚蠢也非常生气,他说:”也许宪章应该看看”,“也许宪章应该看看这个问题!”。27
1978年4 月 27 日,《七七宪章》中一些更勇敢的人们成立了《保卫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为了保护宪章,VONS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其主要目标集中在那些法庭上被起诉或者因其信念而被监禁的人们。1978年最初成立时,它有17名成员。1979年底,这个团体的多个创始人受审并获刑——哈维尔(四年半)、本达(四年)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彼得·乌尔(五年)、伊日·迪恩斯特比尔(三年半),如此重创并没有扑灭这个团体的声音,其成员也在增加。1987年底,VONS已经发布了约700份编号的书面公报,每份公报都包含一个关于迫害或起诉案件的简要报告。而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VONS还会发布新的文件,表彰相关法院(例如第479、502、507号)。28
VONS的公报及许多《七七宪章》文件都发表在一份叫做《宪章通讯》(INFOCH)的刊物上面,这份Samzdat的刊物也不能算作七七宪章的官方出版物,其主要编辑只是宪章签署者彼得·乌尔夫妇。在乌尔入狱5年期间,《宪章通讯》也没有中断过,他妻子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封面上。出版周期原则上每月一期,但是前后时间略有变化:有三周内 1 次(1978-80;1986-87);有每月 1 次(1981-85 年);也有2 周内 1 次(1988 年),看起来1988年最为活跃,这时已经接近天鹅绒革命的大门了。1978 年至 1989 年间,《宪章通讯》共出版了 189 期,刊登了约 4,120 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该刊正式停刊是1992年,在最后三年内(1990、1991、1992)全年只出版了一期合订本,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有一份资料显示,1988年底10期到22期可以邮购,一份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为10克朗29。
宪章成员中还有其他的自选动作。签署者中有大批前共产党员、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一支十分强劲的称之为“独立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鲁道夫·巴泰克(Rudolf Battěk,1924——2013)。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却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1971年因发起“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会主义运动”及散发传单被官方判刑三年半,1980年又因为《七七宪章》和VONS再次入狱,加起来共获刑10年。勇敢无畏的巴泰克和本达在1988年10月发起《公民自由运动》(HOS),其宣言《人人享有民主》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涉足政治的时候到了。”该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废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包括民主、政治多元化、经济繁荣、保护环境、信仰自由、独立工会等12项诉求,可以说是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该宣言共有120名公民签署, 哈维尔、海达内克、萨巴塔等许多签章签署者都在这份签名名单上面30。接下来是警察的又一轮疯狂发作,每一位签名者都遭到了盘问。但这时候整个社会都在觉醒,权力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
从1988年起,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气氛发生了明显改变。在《七七宪章》的催化下,大约30多个独立公民倡议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它们或者是在《七七宪章》签署者带头及影响之下成立,或者是在《七七宪章》的羽翼之下成长起来,其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有些团体较早便存在,但是在这个期间得到进一步更新和充实。
尤其是有一些年轻人的团体,她/他们在1988、1989年一系列的抗议中走到了前头。比如生于1965年的《七七宪章》签署者露丝·索尔莫娃(Ruth Šormová),她有参加教会活动的经历并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1988年4月她与同龄人一道于创立了叫做“独立和平协会”的公民团体(IPA),以民间的名义倡导和平。198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纪念日,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小公民团体与《七七宪章》并肩发起了游行,大约有10000人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再者,198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在布拉格爆发了大规模公众集会,这是“七七宪章”与一个叫做 “波西米亚的孩子 ” (Children of Bohemia)的公民组织共同发动,参与发动者也包括巴泰克的HOS和“独立和平协会“。“波西米亚的孩子”这个怪名的组织于1988年成立,由年轻的反共反对派人士组成,它有一个半讽刺性目标,说是要在波西米亚王国恢复国王,来保障弱者的权利,对抗强者和富人,并保护自然及全面重建经济。不管怎么说,这个组织在88年底和89年组织和参与了许多大规模示威活动。
这里不妨再举出一些当时颇具影响的公民组织31——
捷克斯洛伐克音乐家联盟爵士乐部(Jazz Sec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Union of Musicians)成立于1971年。旨在促进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出版有关文化问题的期刊和书籍,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爵士乐联合会。1984年该组织的活动被禁止,其领导人被监禁。1988年,它以艺术论坛(Art Forum)的名义重新出现。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团结会(Polish-Czechoslovak Solidarity)1978年非正式成立,1981年正式成立。通过定期会议和波兰语和捷克语的联合公报,旨在促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运动之间的合作。1987年,该组织由 “波兰-捷克友谊圈 “( Circles of Friends of Polish-Czechoslovak Friendship)得到补充和壮大。
民主倡议(The Democratic Initiative,1987年秋季)本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传统和东欧的当代改革精神开展工作,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进行广泛的改革来实现民主化。1989年9月,它宣布自己是一个政党,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多元化国家的方案。
美国之友协会(Association of Friends of the USA,1988年3月),旨在促进和美国的友谊。
马萨里克协会(Masaryk Society ,1988年初),旨在让公众熟悉第一共和国总统马萨里克的生活和工作,并组织关于马萨里克的学术研究。
世界和平(Peace on Earth,1988年10月),这是一个来自天主教的团体,旨在推进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
东欧新闻社(East European Information Agency,1988年12月),旨在传播和分享传播有关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信息。
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John Lennon Peace Club,1988年12月),在其为和平而战的总口号之下,同时发展另类文化和与其他独立倡议的合作,并组织了许多反对活动,例如示威或释放政治犯的运动。1989年6月,该团体成员在查理大桥上组织论坛,举办纪念中国1989年天安门和平抗议运动受害者的追悼会。
公开对话论坛( Open Dialogue,1988年8月),旨在创建一个艺术家之间自由交流的平台,打破官方和非官方艺术之间的障碍。
社会防卫倡议(Initiative for Social Defence,1988年10月),旨在为那些遭受歧视或在其他方面受到伤害的人提供援助。
法律援助俱乐部(Club for Legal Assistance,1989年2月)旨在公布违反法律的起诉案件并支持受影响的人,逐步建立一个公共监督系统,以维护合法性和法律秩序。
欧洲之家(For a European House,1989年3月)旨在促进欧洲共同家园的理念,这也是在《七七宪章》经常涉及的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往哪里去的问题。
布尔诺论坛(Brno Forum,1989年1月),旨在唤醒公民生活,打破异见运动与社会的隔阂,以及反对破坏环境的高速发展。
幸福生活协会(Society for a Happier Present,1989年5月),通过具体行为(比如每周一次为在押的政治犯跑步),引起人们对审判和其他形式的压迫的关注。
独立生态团体(Independent Ecological Group,1989年5月),旨在引起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
劳工团结团体(Group for Labour Solidarity,1989年5月),旨在引起人们对于工人问题的关注。
基督教人权联盟(Christian Union for Human Rights,1989年5月),基督徒联合团体,旨在支持被其他团体忽视的人权,例如未出生婴儿的权利,反对色情和性虐待。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for Czechoslovak-Hungarian Democratic Cooperation,1989年8月)旨在阐明两国的真正利益,并克服两国政府之间的暂时分歧。
释放斯洛伐克民主人士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Release of Slovak Democrats,1989年8月),旨在为斯洛伐克囚犯辩护,抗议新的审判。
独立知识分子圈(Circle of Independent lntelectuals,1989年9月),旨在恢复欧洲文化的价值,支持社会各阶层的对话。
捷克斯洛伐克无政府主义者协会(The Czechoslovak Association of Anarchists,1989年10月),旨在继续开展85年前成立的捷克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活动,并代表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
绿色俱乐部(The Green Club,1989年9月),目标是寻求限制对环境的破坏,支持健康和生命的权利。
青年独立协会 (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Young People,1989年10月),旨在维护年轻人的权利和利益,寻求建立一个自由的青年组织。
当然,在所有这些公民团体中最著名的、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是公民论坛 (Civic Forum,简称OF),1989年11月19日成立,哈维尔是其创始人和领导者,这是一个许多团体和组织的联盟,包括《七七宪章》、捷克斯洛伐克赫尔辛基委员会、VONS、公民自由运动、独立社会主义团体、独立的学生协会、公开对话论坛、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倡议、独立的和平团体、捷克斯洛伐克笔会中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教会代表,甚至还有共产党的个人成员。成立当天,OF提出的目标是——与国家当局谈判,要求与1968年苏联干预及警察对示威公民采取行动有关的共产党领导人辞职,并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些行动,包括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论坛还发表了一份详细的原则,以克服该国的道德、精神、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很快,公民论坛成为领导天鹅绒革命的核心。与公民论坛并肩作战的是公众反对暴力(The Public Against Violence ),1989年11月20日成立于布拉迪斯拉发,与公民论坛相似,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反对派组织。
2023年2月10日
—————
本文注釋:
1 Pankaj Mishra“Václav Havel’s Lessons on How to Create a ‘Parallel Polis’”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vaclav-havels-lessons-on-how-to-create-a-parallel-polis.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该文。
2 Va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见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London:
3 Faber & Faber, 1991),259-260. Daniel Brennan :”Reading Václav Havel in the Age of Trump “,Critical Horizons,A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Volume 20, 2019 – Issue 1, Pages 54-70 | Published online: 17 Jan 2019,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409917.2019.1563997?journalCode=ycrh20 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该文。
4该访谈1986年以捷克文在伦敦出版,书名为《远程审讯》(Dálkový výslech)。英文版为 “Disturbing the Peace”,New York : Alfred A. Knopf,1990,中文版《哈韦尔自传》,李义庚、周荔红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
5 Vaclav Havel”Disturbing the Peace”, Translated by Paul Wilson, London:Faber & Faber,1990,133.
6 海达内克第六封信(1977年3月19日), https://www.hejdanek.eu/Archive/Detail/884
7 同上
8 Jan Patocka“ What Charter 77 is and what is not” : “The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oral area and the state might point to the fact that Charter 77 is not a political act, that it is not in competition with or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the sphere of any political function. Charter 77 is not a club or an organization – its base is only the individual; moral obligations, ensuing from this association have the same character”. 见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 The Documents ofCharter’77https://www.csce.gov/sites/helsinkicommission.house.gov/files/Human%20Rights%20in%20Czechoslovakia%20The%20Documents%20of%20Charter%20%2777.pdf
9 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 Palgrave Macmillan ,1991.35—41,下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该处。
10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Powerlsee,” 见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London:Faber & Faber, 1991),192.
11 同上194
12 同上195
13 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 Palgrave Macmillan ,1991,“Preface”,10.
14同上,57。
15 同上,44
16 同上,52
17 同上,64
18 同上,50
19 同上,100
20 同上,111
21 同上,65
22 同上,57
23 同上, 92。
24“ KOR”1976年9月创立,被认为是波兰乃至东欧的第一个反对派民间组织,它的原名是“保卫工人委员会”,最初旨在为当年在拉多姆和华沙的抗议遭到报复而被捕的囚犯及家人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虽然KOR的成员先后遭到官方各种报复,然而他们的努力在第二年春天得到了回报——1977年春天,官方被迫大赦罢工的监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也由此更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
25同上, 62—63。
26 Michael Zantovsky“Havel:A Life”,Grove Press,New York,2014,288
27 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 Palgrave Macmillan ,1991,76。
28 H.Gordon Skilling“Samizdat and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Columbus,1989,46
29 http://scriptum.cz/cs/periodika/informace-o-charte-77
30 http://www.csds.cz/cs/g6/4806-DS.html
31 这份独立组织的名单来自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y Europe: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 Palgrave Macmillan ,1991,114—118
由于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民主季刊》资金来源变得不稳定。如果您认同季刊的价值,请打赏、支持。当然,您可以点击“稍后再说”,而直接阅读或下载。谢谢您,亲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