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於捷克的「七七憲章」(1977)運動,中國知識界的關注多集中在哈威爾等公開人物,對於「七七憲章」運動更詳細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細節,卻鮮為所知,包括在這個運動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捷克前共產黨人和捷共前高層。東歐異議思想研究學者崔衛平在一次閱讀中,偶然發現一篇關於捷共前高層茲德涅克·姆林納日(Zdeněk Mlynář, 1930-1997)的文章,發現他竟然也是「布拉格之春」改革設計師和《七七憲章》重要締造者之一。於是從姆林納日(1930-1997)的思想和活動入手,崔衛平詳細考察了其在「七七憲章」運動前後的活動與貢獻,並以此澄清中國知識分子對憲章的誤解:憲章非頂層設計或制度替代,而是中立對話工具,淡化意識形態。而姆林納日經歷象徵從黨內改革到持不同政見轉變,這不僅豐富了「七七憲章」運動的脈絡,也顯示了社會主義反對派在東歐異議中的深層作用。
本文原載《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思想》雜誌和崔衛平教授授權轉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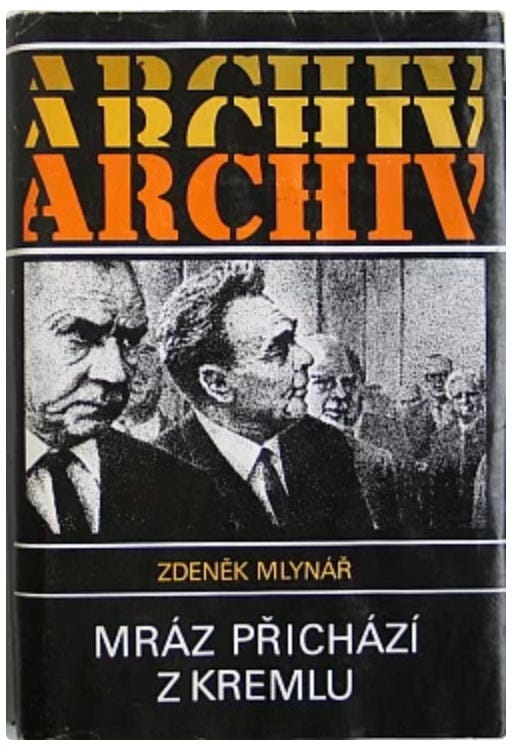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知識界對興起於70年代的捷克「七七憲章」運動一直保持關注,但受資料和其他條件所限,這種關注也僅限於像哈威爾這樣的少數公開發言人及歷史大事件中的人物;對於「七七憲章」運動更詳細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細節,卻鮮為所知,包括在這個運動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捷克前共產黨人,包括捷共前高層。
2021年夏天,在完成其他事務之後,我又回到了自己心愛的東歐反對派這個話題,尤其是與哈威爾有關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
我始終好奇到底是哪些人們發起了《七七憲章》,關心這個名單背後所蘊含的反對派的起點、價值立場和社會脈絡,想要知道這股反對能量的匯聚、傳遞、轉化和最終走向。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了一篇獨特的文章〈茲德涅克.姆林納日與尋找社會主義反對派:從活躍的政治家到持不同政見者再到流亡編輯工作〉。1 其主角姆林納日(Zdeněk Mlynář, 1930-1997),1968年8月捷共十四大選出的中央主席團成員(相當於人們熟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竟也是《七七憲章》的重要締造者之一。該文所發掘和梳理的豐富史實,直接戳到了我多年的盲區:在我起初接觸和介紹哈威爾及《七七憲章》時,基本上沒有注意到這個人,沒有從他那裡獲得任何延展的脈絡,他的名字中文很難發音應該不是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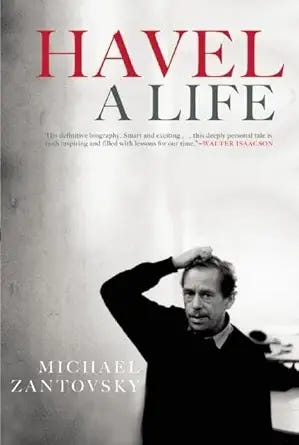
即使在哈威爾的筆下,姆林納日也多有提及。哈威爾於80年代中葉接受流亡劇作家卡雷爾.赫維紮拉(Karel Hvížďala)的長篇訪談,2 關於他本人跌宕起伏的過往生涯,其中有一處,哈威爾這樣寫道:
尤其令我緊張的,原定4點鐘聚齊,可以到了5點,仍不見帶著前共產黨員簽名名單的茲登涅克.姆林納日的影子。後來才弄清楚關於時間問題有個小小的誤會。他終於帶著100多個簽名來了,這個數字真令我大吃一驚。因為第一批簽署者一共才243人。警方並未露面,順利地處理好各項事務後,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喝了香檳酒以示祝賀。3
姆林納日帶來了140個簽名。在第一批簽署者中,比較起其他政治光譜或團體,前改革派的共產黨人占了絕對多數。這位姆林納日是「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設計師,杜布切克智囊團重要成員。1968年在蘇軍坦克入侵之後當年11月,便主動辭去了捷共黨內的所有職務,1970年被開除出黨。此時被貶謫在國家博物館的昆蟲研究所,每日面對花花綠綠的毒蟲子。
哈威爾筆下還提到了姆林納日參與1976年秋天那場聲勢浩大的聲援搖滾音樂人活動。姆林納日先是與被罷黜的外交部長伊日.哈耶克(Jiří Hájek, 1913-1993)一道,簽署了由哈威爾等人發起的寫給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公開信。這位哈耶克是「布拉格之春」之後第一批倒下的捷共高官。入侵時他在南斯拉夫訪問,轉身他去了聯合國譴責蘇軍暴行。此刻,兩位來自前共產黨陣營的高級官員,還為給伯爾的公開信在前共產黨人那裡徵集到了60個簽名,讓人感覺像是一場雪崩。這封公開信發表在1976年8月28日的《法蘭克福總匯報》,9月6日,伯爾在同一刊物上發表回信,令國內聲援的人們士氣大振,迫使捷克官方不得不推遲了法庭審判的日期。
9月8日,姆林納日在海外流亡雜誌《信報》(Listy)發表署名文章——〈反對虛假和謊言:致捷克斯洛伐克負責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官員的公開信〉。與哈威爾反覆強調的「真實」略有不同,姆林納日用的是「權利」這個概念,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問題,他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這種反叛方式是否是擺脫人類生活危機狀況的一種可能方式,而是他們是否有權利在自己的生活中嘗試找到一條他們認為真實而有價值的出路。」此處的「公民權利」以及它所包含的法制秩序的要求,是68年「布拉格之春」中,人們反思50年代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改革的共產黨人從自身經歷中得到的重要教訓,相關討論姆林納日都身在其中,他本人亦來自法律背景。哈威爾認為這篇文章是前共產黨官員通過姆林納之口表達了他們的共同看法,會給黨內高級官員帶來巨大衝擊。
審判搖滾音樂人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遵守《赫爾辛基協議》的壓力之下,法官允許庭審向公眾有限開放,大約有150人參加,卻只被允許進入法庭走廊和樓梯,不允許進入法庭。這麼多前來圍觀呐喊的人們,來自不同的圈子,有著不同的身分,前共產黨人、自由派知識分子、天主教或福音教派人士,各種名目的激進的或者溫和的改革派人士、社會主義者。許多人互相之間從來沒見過面,但是此刻人們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和隔閡,毫無顧忌地互相信任和交談。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白髮蒼蒼、年已七旬的老先生弗蘭蒂謝克.克里格爾,這位資深反法西斯戰士,在蘇軍入侵之後被擄到莫斯科的捷共中央代表團裡,是唯一一個拒絕在《莫斯科協議》上簽字的人(下面還要談到他)。姆林納日也到場了,他走出了森嚴壁壘的共產黨等級制度,來到了不受體制保護的「不體面」的人們中間。「聚集在法庭外面的人群就是七七憲章運動的原型」(《哈威爾自傳》, 頁116)。哈威爾曾說,當時他感到有一種迫切的願望,想到要搭建一個公共平臺,能把這股剛剛聚集起來能量保存下來,形成有持續影響的力量。
關於搭建平臺,有人在考慮類似的事情。1975年8月,由35個歐洲和北美國家共同參與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制定和通過了《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Final Act),美國、加拿大、大部分歐洲國家及蘇聯陣營一併簽署了這項協定,捷克斯洛伐克也在其中,「人權」是這個協議中一個富有特色的重要內容。起初,對該協議國際上和各國內部反應不一,被罷黜的捷共改革的共產黨人卻率先表現出熱情。協定簽署的第二個月即1975年9月,姆林納日便邀請哈耶克一道上瑞典電視臺接受訪問,公開表達支援該協定內容。接著他們兩人與歷史學家卡雷爾.卡普蘭(Karel Kaplan)便想弄一個人權委員會,用以監督捷克斯洛伐克當局落實《赫爾辛基協議》的結果。這個計畫不僅在捷克國內流傳,而且也傳到了海外流亡者那裡。哈威爾在《自傳》裡也說過,這個擬議中的委員會打算請哈耶克擔任主席,後來大概是因為缺乏有行動力的人而作罷。運用國際社會提倡的「人權」概念,對捷克斯洛伐克被罷黜的前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在法律框架裡討論問題的思路。既然捷克政府簽了這項包含人權內容的協定,那麼對於官方權力這便是一個約束和壓力。
1976年12月10日,即「七七憲章」第一次會議,在歷史學者文德林.科梅達(Vendelín Komeda, 1946-1995)的牽線下,這兩批人見面了,在布拉格繁華大街的一個單元裡,與會者一共有5個人:姆林納日、哈威爾、編輯和散文作家伊日.涅梅克 (Jiří Němec, 1932-2001,哈威爾當時形影不離的朋友)、劇作家帕維爾.科胡特(Pavel Kohout, 1928-)及會議的組織者科梅達。會議本著對話的精神進行,存在幾種不同意見,其中有呼籲國家履行其義務(運用現有體制框架施加壓力);或者弄一個像波蘭不久前成立的KOR那樣的民間開放組織(體制之外);以及遵循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Tomm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小範圍工作」的方針(較少給當局施加壓力),也包括展現出更加鮮明的、富有挑戰性的政治立場。應該說,「七七憲章」中的前共產黨人與非共人士始終存在某些分歧,但雙方無意誇大這種分歧,而是小心翼翼地在一起尋找共同語言,儘量磨合,至少在一開始是這樣。
據哈威爾的回憶,他本人是在第一次會議結束之後,與涅梅克一道走訪了哲學家拉迪斯拉夫.海達內克(Ladislav Hejdánek, 1927-2020),後者提醒他「可以以不久前頒布的人權公約為基礎」(《哈威爾自傳》,頁117)。哲學家海內達克與涅梅克的友誼始終為人稱道。涅梅克有左翼天主教背景,而海內達克是左翼福音派教徒,他倆在哲學、宗教和政治領域親密合作數十年。
《七七憲章》誕生的第二次會議(12月14或15日)有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大名鼎鼎的資深刺蝟型作家路德維克.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 1926-2015,1967年被開除黨籍)、年輕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佩蒂.烏爾(Petr Uhl, 1941-2021),哲學家揚.帕托切克(Jan Patočka, 1907-1977)派來了他的代表,姆林納日則帶來了哈耶克本人。上回的中間人科梅達這一次是作為「獨立社會主義」的代表,因為他們的領導人巴泰克剛從監獄出來,擔心員警跟蹤沒有到場。
這是一次決定性的討論,產生了七七憲章的基本框架。目前最權威的哈威爾傳記作者、曾任哈威爾總統的新聞秘書及駐美、英大使邁克爾.贊托夫斯基(Michael Žantovský, 1949-),寫到了目前保留下來的第一份憲章草稿(1976年12月16日),從中已經見出《七七憲章》定稿之後的主體部分已經成型,即將捷共當局對於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與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的實際現實進行對比,並指出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這份草稿還提到想要成立一個「人權委員會」(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來監督和宣導尊重上述公約和國內立法所保障的權利」,4 這與傳說中的姆林納日沒能實現的計畫如出一轍,也符合第一次會議中已經出現的要求「國家履行其義務」這個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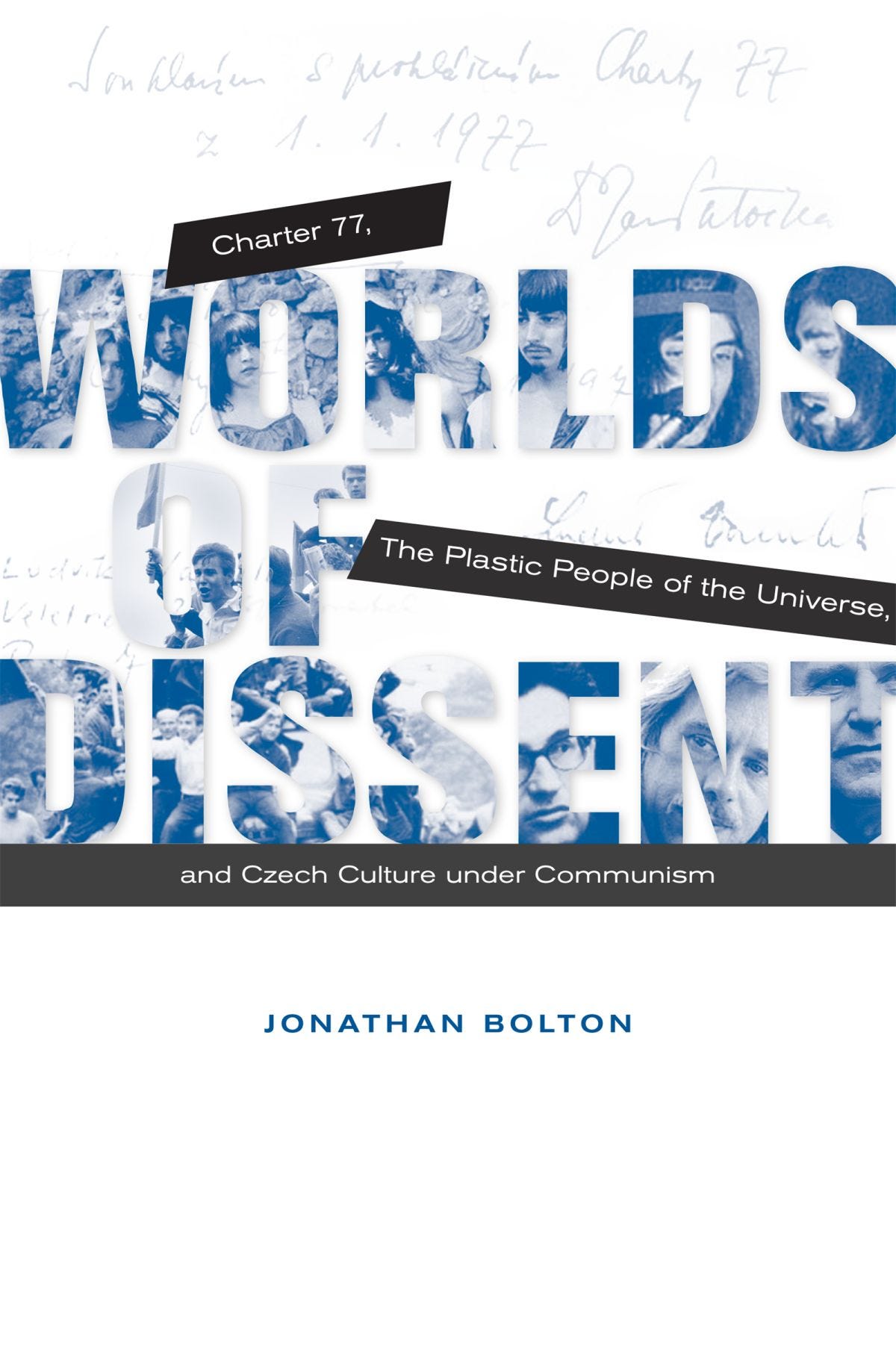
因此,關於憲章中的「人權」主題是如何確定的,我越來越同意姆林納日的說法——「訴諸(人權)公約的想法,來自被驅逐的改革派共產黨人反對派這一邊。」5 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也沒什麼爭議,只是此前人們沒有直接說明。1996年,哈威爾在接受捷克電視臺關於製作紀念《七七憲章》20周年紀錄片訪談時,也明確說到了是「他們更早想到了這個問題」。關於前共產黨人與赫爾辛基人權條約之間的深沉脈絡,我們在下面還會談到。
「七七憲章」這個名字是科胡特的主意,他也是自始至終的參與者。但誰是《七七憲章》起草者,姆林納日及前共產黨人這條線,顯然被淡化了。哈威爾曾在第一時間,向員警承認《七七憲章》是他本人起草的,體現了承擔責任和風險的高風亮節。為了強調《七七憲章》集體創作和負責的精神,哈威爾也始終沒有說出在討論時誰在其中增添了或刪去了什麼。但有記載,當他接受赫維紮拉的遠端採訪時稱「我在這裡不會說誰具體寫了第一個憲章宣言的文本,我只會回憶誰參與了起草:我,姆林納日和科胡特」。但不知為什麼,這個長篇訪談在正式發表時這三個人的名字都被刪掉了,6 只保留了前一句(「我在這裡不會說」)。關於這三個名字的說法,另有一個旁證,邁克爾.贊托夫斯基在哈威爾傳記中也寫道,當時討論時保留下來的草稿中,其中有一份提到《七七憲章》文本的責任人有三位——哈威爾、科胡特和姆林納日。贊可夫斯基還特別提到,「姆林納日是起草者中唯一一位律師」。(2014, Michael Zantov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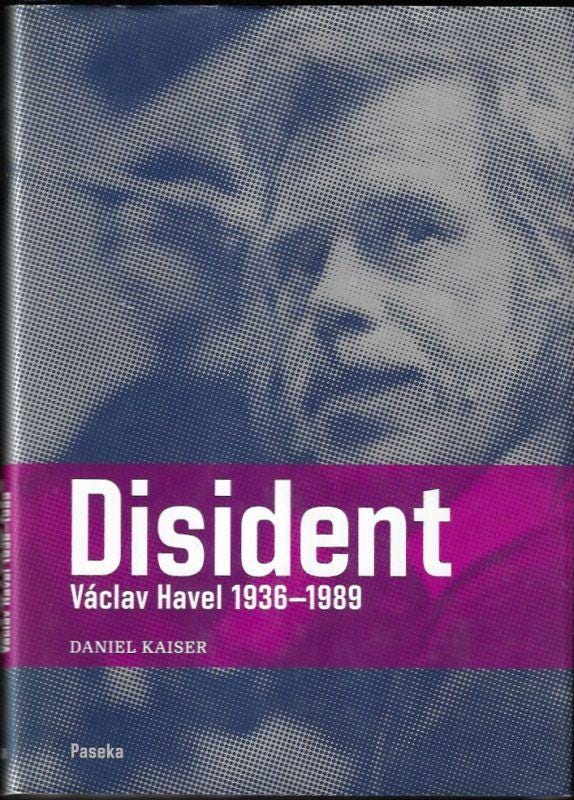
哈佛教授喬納森.博爾頓(Jonathan Bolton)在他這本豐富多彩的《異議的世界——七七憲章、宇宙塑膠人、共產主義下的捷克文化》一書中,分析過《七七憲章》的措辭,也幫助說明了前共產黨人的深度參與。通曉捷克文和斯洛伐克文的博爾頓教授寫道,《七七憲章》「文中幾乎沒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修辭手法或豐富多彩的轉折。其基本語氣是不帶感情的研究口吻,沒有悲愴、憤怒或激動的情緒。儘管它比共產黨的標準政治文本——無論是黨的指令,還是《紅色權利報》社論,或者是「五一」演講——都要清晰簡潔得多,但它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捷克官僚主義色彩,甚至還有一些行話,如pokrokové sily(進步力量)或humánní vývoj(人類發展) 」(2012, Jonathan Bolton)。應該不只是姆林納日,哈耶克也到現場參加過討論,不排除某些字眼來自他。收在約翰.肯尼1985年編輯出版的這本《七七憲章》簽署者自述的書裡,有一篇哈耶克的文章,標題則是〈人權運動和社會進步〉。7「進步」或「社會進步」,是姆林納日找來那100多位改革的共產黨人的共同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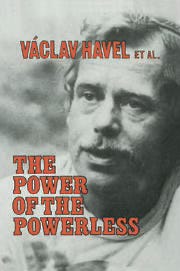
為了防止文本洩露,徵集簽名時準備了六份影本,由徵集者當面給對方看,看完後收回文本,署上自己的名字則是在另一張空白紙上。這六份影本,哈威爾拿走了一份,他的徵集對象是作家和藝術家,涅梅克拿走一份,徵集對象是新教和福音派知識分子,烏爾拿走一份,徵集對象是前政治犯和青年運動人士,姆林納日拿走了三份,他的確沒有辜負他拿走了最多的憲章樣本。從保存下來的檔來看,秘密員警似乎早在第一次會議期間就通過對科胡特公寓的竊聽得知了此次行動的準備情況,但直到1977年1月6日,他們才知道文本的確切措辭或簽署人數。這天哈威爾和他的幾位朋友想要把帶著簽署者名單的《七七憲章》文本郵寄給官方有關部門和其他簽署者,結果一行人被員警截在了郵筒旁,同行的蘭多夫斯基1968年前是一名深受歡迎的戲劇和電影演員,此番他與員警衝突的場面有路人看到,人們以為自己喜歡的偶像又復出拍電影了。
「七七憲章」最終並沒有弄成一個有著固定人馬的委員會,像蘇聯的赫爾辛基小組那樣,而是本著「認同其主張、參與其工作並給予支援」的精神,採取開放式簽名,更像波蘭的KOR(保衛工人委員會),8 這一點應該是哈威爾等非共人士的主張。鑒於「七七憲章」既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組織,締造者們最終決定了它「公民倡議」(civic initiative)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七七憲章》被中國讀者誤解了。它完全不是一份來自民間的關於這個國家的頂層設計,不是關於這個社會制度前景的替代方案,這些正是所有參與者所要避免的,甚至也不是一份反共宣言。當這些人決定以「法律/人權」作為核心,同時意味著淡化意識形態,甚至暗含了意識形態的中立性,它限定自己的意圖和活動範圍是「與黨和政府當局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七七憲章宣言》)。
從一開始,「七七憲章」就有三位發言人的規定,他們來自前共產黨人、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這三個不同領域。從中也可以見出,這是一個多元化的平臺,具有足夠的覆蓋性。這些不同派別達成的重要的一致意見還有,不論什麼組織形式,其形式必須是多元化的,每個人、每種政治立場之間都是平等的。任何派別,無論在過去多麼強大,但是在新平臺裡面都不能有任何特殊位置。這意味著——在即將形成的新社區中,前共產黨人也不能占據主導地位,任何人不能在《七七憲章》上面,打上他們自己意識形態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哈威爾對於姆林納日給予了高度評價:
對許多共產黨員來說……這是邁向生活的一大步,是真正為共同的事業著想的一步,其代價是擯棄「黨的領導地位」這一原則。實際上前共產黨員中贊成這一口號的已為數不多了,但是有些人在骨子裡和潛意識裡仍保留著這一概念。茲登涅克.姆林納日在這方面應該受到高度讚揚。他以自己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看清了形勢,迅速跨出這一步並以自己的威信影響著他周圍的人也跨出了這一步。(《哈威爾自傳》,頁122)
哈威爾所說的姆林納日的「威信」,建立於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共產黨高級官員中,姆林納日的經歷似乎過於單純。戰後的1946年,16歲的姆林納日加入了共產黨。他稱自己伴隨著戰爭而成長,在一種極端對立的條件下形成了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世界觀。1950年到1955年,姆林納日在莫斯科大學法學院學習,與戈巴契夫成為同班同學,而且同住一個宿舍,兩人成為好友,有過許多深入長談。1953年他倆一前一後排在向史達林遺體告別的隊伍裡,在同一個禮堂的追悼會上體驗了史達林離去的恐懼不安,同時意識到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必須改變,由此而產生了對於未來新的希望。9回國之後,姆林納日一直在法律部門工作。1955年他擔任布拉格總檢察長辦公室的部門主管,1956年加入捷克社科院「國家和法律研究所」,1964年姆林納日擔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法律委員會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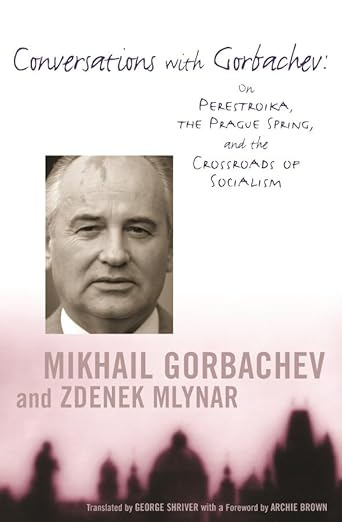
1966年姆林納日被任命主持一個跨學科的專案「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和政治制度的發展」,這個項目的研究成果最終體現在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行動綱領》(又稱《四月提綱》)之中。該綱領集中體現了「布拉格之春」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限制過於集中的共產黨權力、引進市場經濟、恢復被迫害者的名譽、擴大言論和藝術創作的自由、捷克與斯洛伐克的聯邦制等。著名經濟學奧塔.希克(Ota Šik, 1919-2004)主持了經濟改革部分,他的方案曾讓布拉格街上四處跑著私人計程車,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道特殊風景。拉多萬.里奇塔(Radovan Richta, 1924-1983)主持「科技革命對社會和人類的影響」部分,正是此人於1966年提出「具有人道主義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這個概念也被寫進《提綱》之中。姆林納日負責的政治部分在其中題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對社會進行管理的新體制〉。這份《四月提綱》通過的前一天,姆林納日增選為捷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姆林納日還以個人名義發表了多篇署名文章,這篇〈走向社會的民主政治組織〉,被認為是「布拉格之春」的標誌性作品之一,文中用「裝點門面」來形容人們所參加的選舉,在這個空洞的外表之下,人們陷入了「原子化的私人生活」,這造成了民主進程的巨大障礙,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實現政治上的「多元制度」(pluralist system),用來釋放不同人們的利益立場。當然他並不建議馬上成立反對黨,而是推薦充分利用已有的「國民陣線」,來釋放不同的政治力量。在一次公開報導的圓桌會議上,姆林納日甚至用「獨裁統治」(dictatorship)來形容蘇式中央指令,認為「黨必須放棄壟斷性政治主體的地位」(〈尋找〉)。不管怎麼說,當時的捷共與捷克社會是在朝著越來越民主的方向在走。8月20日夜蘇聯為首的華約軍隊入侵,捷共決定提前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8月22在布拉格維索卡尼區一家工廠裡,在工人們的保護下以及頭頂上入侵飛機的轟鳴聲中開幕。這個半秘密的大會一致通過了抗議入侵的聲明。作為改革的政治明星,姆林納日也在這個黨代會上被增選為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
不斷有研究家指出姆林納日對戈巴契夫的影響。1967年夏,姆林納日受戈巴契夫邀請訪問蘇聯,在斯塔夫羅波爾(Stavropol,戈巴契夫任這個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與戈巴契夫夫婦住在一起,兩位老同學有機會討論了當時在布拉格盛傳的改革派思想。第二年蓬勃興起的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姆林納日被罷黜直到發起「七七憲章」,乃至1977年6月流亡奧地利,媒體有許多報導,戈巴契夫看在眼裡。1985年3月戈巴契夫上臺,西方世界很少知曉他,姆林納日在義大利共產黨報紙上發表文章〈我的學生朋友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其中強調戈巴契夫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著獨特理解和思路,因而完全值得期待,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戈巴契夫後來果然做出了驚天動地的舉動,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也是最受低估的政治家。1997年4月納姆利日去世時,戈巴契夫特地前往布拉格,在他的葬禮上發表講話。身為總統的哈威爾也給姆林納日的遺孀發出唁電,稱姆林納日為「是我所遇到的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對手之一」(〈尋找〉)。
為什麼姆林納日此前不進入我的視野?不僅是我,在我接觸的英文資料中,尤其2010年前出版的,對於這位「七七憲章」的締造者也是一筆帶過,他的大部分寫作還是捷克文沒有得到翻譯。但近年來,姆林納日的名字更多出現在年輕史學家的筆下。10很顯然,此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們都被裹挾一個宏大敘事中,那便是所謂「歷史的終結」。如同我們曾熟悉的「歷史必然規律」,這個「歷史的終結」也被高度狹窄化,彷彿只有被選中的少數人才能代表其方向,只有出現在「終結」這個維度上才能獲得意義,其餘只能被歷史無情淘汰。哦,這個對我們太熟悉了,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把某某人、某某勢力「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成為我們的兒歌!但後來,一批批人、一張張面孔又從「歷史垃圾堆」裡走出來,重新找到了我們。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有許多記憶被沉埋地下。當我讀到米奇尼克說,「我們這一代人記得某些名字是如何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照片中消失的」,深有同感。米奇尼克近些年的文章火力不減,大多落在了今天的「反共人士」身上,他發明了一個說法叫做「帶著布爾什維克面孔的反共病毒」(the virus of anticommunism with a Bolshevik face),這些人認為自己同過去的歷史沒有關係,因而民族的歷史應該從他們開始。對此,米奇尼克針鋒相對地指出,共產政權最初出現和稍後的那些年,「正是從這些最初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中,出現了對共產主義最有洞察力、最勇敢、最持續的批評者。」11
「持異議者」(dissident)這個概念的運用,也是一個原因。這個主要是西方記者創造出來的詞,除了挑戰現有政權,一般還有這樣幾層含義:1. 在官方的權力和政治結構之外,尤其是黨外人士;2. 從事某種非法的地下活動,包括寫作和出版乃至團體(如果有的話);3. 親西方,或者被視為是親西方,在冷戰的條件下,「反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站在西方的立場上。在這些「持異議者」所處環境裡,官方權力也千方百計在公眾面前把這些人說成是想要走西方道路——「復辟資本主義」。正如68年經濟改革家奧塔.希克所指出的,「反共並不必然意味著親資本主義」。實際上,他說,恰恰「是共產主義的宣傳機器發明了『反共』這個怪物,旨在阻遏對於這種反人類制度任何嚴肅的批評」。寫下這些時,這位布拉格「經濟改革之父」已經流亡瑞士,他的這本《第三條道路》是他自己的思想總結,也是寫給西方讀者的。他告訴人們,他原來所處的社會「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樣遠離社會主義。而那些對這個問題還抱有幻想的真誠的西方年輕人,總有一天會發現,共產主義國家其實是反社會主義的」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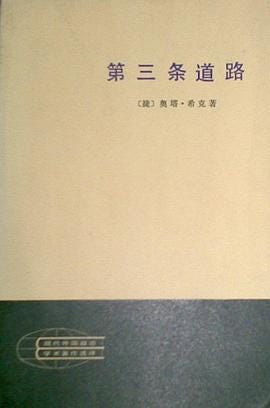
最初接觸東歐反對派,我就發現他們始終是把「共產政權」、「共產國家」、「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區分開來,並對「社會主義」採取肯定的態度和抱有好感;我也很快感覺到,讓我身邊的朋友接受這一點並不容易,儘管有哈威爾這樣的權威。1975年哈威爾在寫了一封給當時的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之後,接受採訪時說「我把自己視為社會主義者。我甚至認為自己從馬克思主義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但從來沒有認同過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我從來不是共產主義者」。13放在那個環境中,哈威爾其實是進了一步——他平時的主要立場是自由民主派,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尤其是,作為百萬富翁的兒子,他被排除在正常社會生活之外,也許連宣布自己社會主義立場的資格也沒有,除非到了1968年朝向民主的社會主義旗幟被捲進坦克履帶之後,即一大批共產黨內的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也「墜落」到他這個位置上之後。
提醒哈威爾運用國際人權條約的哲學家海內達克,也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甚至有著宗教背景;他也一直在思索社會主義的問題。1968年在他導師揚.帕托切克的舉薦下進了捷克社科院當哲學研究員,1971年在肅清中被開除。這年秋天,他因參加「公民社會主義運動」被捕入獄9個月,他在法庭上自我陳述道——出於宗教動機,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支持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1978年哈威爾寫出〈無權者的權力〉,本來有計劃圍繞著哈威爾的話題在反對派內部進行廣泛討論,因此又約請了一批人接著寫文章。新教背景的海內達克並沒有直接回應哈威爾在那篇長文中提出的問題,而是覺得自己應該寫一篇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於其中他寫道:
社會主義是自由民主傳統的產物,它遠不能預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也不能像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歷史合理性在於它將民主原則推廣到社會和經濟領域,並將其付諸實踐。社會主義是民主在各個領域的全部體現。……目標不應是分享權力,而是迫使當權者走上合法和正當的道路。 民主和社會主義都植根於歐洲,不僅植根於歐洲的政治傳統,更植根於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傳統。14
海內達克的這些表述,對我們這些從小在課堂上從蘇式教科書了解社會主義、考試前狂背「人類歷史發展五個階段」的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這位海達內克睿智而富有勇氣,在反對派中享有崇高聲望。當他的老師帕托切克在憲章發布兩個月後遭受長時間審訊而去世,海達內克接替了憲章發言人的位置,在最困難的時刻挺身而出。1980年,海達內克再度擔任「七七憲章」發言人。他花四年時間寫的《給朋友的信》,探討所謂「正常化」時期人們的精神上困境、道德上的可能性及「七七憲章」的性質和意義,日後成為「七七憲章」的重要精神文獻。天鵝絨革命之後,哈威爾邀請他擔任1989年12月到1990年6月大選之前這段「民族諒解政府」時期的副總統,被他拒絕了。
比起哈威爾、海達內克這些非黨人士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更為明顯的是,更多從蘇式共產政權中跌落出來的人們,則表現為後退一步。那些前共產黨員,當他們從體制之內滑落,也是他們從自己的政治語言中清除共產主義教條和戒律的開始。此前體制專屬的詞彙,表面上空洞浮誇,背後卻隱藏著一種獨特的實用主義,可以用來互相識別及利益交換,比如哈威爾分析過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這些被罷黜的人們不再運用體制的力量發揮作用,他們也沒有必要繼續使用這種語言及立場。較早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學者弗拉迪米爾.庫辛(Vladimir V. Kusin, 1929-)描述過這個變化,他指出:68年之後, 「曾經用 『共產主義』來指稱一個人的世界觀,已經被『社會主義』所取代。」15那麼,什麼是撤退之後的「社會主義」?
很有可能,從共產主義撤退下來的社會主義,與哈威爾這樣的非黨人士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的那個位置,是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中同一個關於社會主義的吃水深度或基本共識。實際上在我這個遙遠的東方人看來,整個一場「布拉格之春」,甚至也可以看做蘇聯陣營中的國家 「共產主義」朝向「社會主義」的撤退。「布拉格之春」(從杜布切克1968年1月上臺到8月20蘇軍坦克進來)是後來追認的說法,身處其中時,人們稱其為「復興進程」(obrodnému procesu),有點像我們的1978年時「改革開放」,當然不盡相同。當人們說保守派企圖阻擋「復興進程」,就像我們這裡所說的有人試圖反對改革開放。不同的是,處於歐洲中心的這個小國家1968年出現的風暴,正是有著一個朝後看的面向,在他們自己看來,是回到和重新進入某個已有的脈絡之中,接續上某個不幸遇到中斷的傳統,這才稱得上是「復興」或「再生」。這就比較有意思了。也許,蘇式共產主義對他們來說是外來的,但是社會主義不是;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本土所誕生和生長出來的。
拉開距離看,不管是在「布拉格之春」或哈威爾或海內達克那裡,人們都可以清晰地聽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國之父湯瑪斯.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思想的回聲,他於1918-1935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馬薩里克不能算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對於社會主義情有獨鍾。他出身於一個貧困家庭,靠自身的頑強努力受到了高等教育,在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兩度當上奧地利帝國議會議員(1891-1893;1907-1911)。在他從西歐到美國四處奔波遊說建國及組建軍隊之前,他是一名編輯和大學教授,一位著書立說的哲學家,曾經是哲學家胡塞爾的哲學引路人和精神導師。16 在擔任捷克布拉格大學教授期間,針對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馬薩里克開設了一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這也可以視為他如此重視馬克思主義,渴望與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對話,該課堂講義1898年先以捷克文出版,很快又有了德文和俄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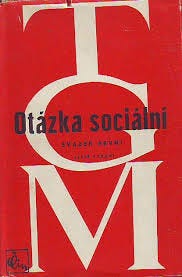
從書名《社會問題》中可以見出,馬薩里克分享著與馬克思同樣的起點。書的開篇他便寫道:「全部經濟和社會苦難的巨大事實,我們所有人眼前始終存在的物質和道德苦難,無論我們看到的是富人的奢華還是無產者的悲慘,無論我們觀察的是城市還是鄉村、街道還是家庭的生活……社會問題意味著今天成千上萬人的不安和不滿、渴望和恐懼、希望和絕望……」年輕時馬薩里克花過許多時間與工人們在一起,為他們舉辦講座,提倡八小時工作制和普選權。馬薩里克畢生對於貧困者和弱者有一種痛徹心扉的感覺,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認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知識、意識和良知的核心」17。
然而,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是,馬薩里克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工人的問題,而是與所有人有關,是關於所有人道德或不道德問題。他的「社會主義」,也不是一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或者關於改造社會的一攬子計畫,而是以倫理思想為基礎,將人道主義理想運用到社會中的人與人關係中去。他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的黑格爾哲學痕跡,即關於歷史的動力、歷史的必然性及使命、結局之說,認為由某個現成的歷史規律來主宰一切,具有一種道德上的冷漠,同樣,馬薩里克也批評自由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在其現代化、世俗化面目中,有其道德冷漠的一面。馬薩里克敏感地注意到了他那個年代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將社會主義與康德哲學相結合的努力,強調社會主義運動的道德動機和個人責任感,他比較認同和欣賞伯恩斯坦。但馬薩里克本人最喜歡用的詞還是人道主義。他明確說過:「我接受社會主義,因為它與我的人道主義計畫不謀而合。我不接受馬克思主義。」18因此,很早(1948年)便有人運用「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來闡述馬薩里克獨特的社會主義思想。
在他去世前幾年,馬薩里克與作家恰佩克就自己的生平經歷尤其是思想過程,有過多次長談,於其中他給出了他自己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
我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愛你的鄰居、愛人類的問題。我不希望存在貧困,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體面地生活,在自己的勞動中,靠自己的勞動,像美國人說的那樣,有足夠的「肘部空間」。愛你的鄰居不是舊式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只是在這裡和那裡提供幫助。真正的人性之愛是通過法律和行動來改變現狀。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我贊成。(1995, Karel Cap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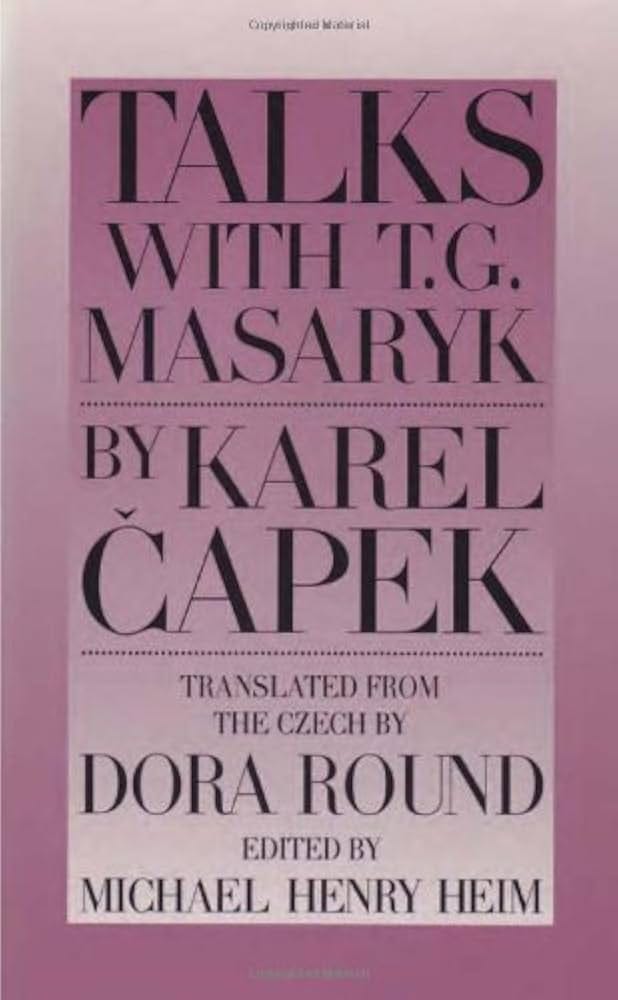
作為民族獨立和共和國的締造者,近20年的總統生涯,馬薩里克無疑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現代民族精神氣質。在他的年代,他把社會主義變成所有人無法繞開的話題。正如捷克文《哈威爾傳記》作者所說的那樣, 「在上個世紀30年代,老哈威爾的朋友中沒有人敢於懷疑社會主義概念。」這裡的老哈威爾指的是哈威爾的父親,百萬富翁本人瓦茨拉夫.馬利亞.哈威爾(Václav Maria Havel, 1897-1979)。在其回憶錄中,他稱自己「贊成社會主義,但那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的那種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2009,Daniel Kaiser)。哈威爾是在父親的圖書館裡讀到了馬薩里克的著作。
錢永祥先生在近作〈魯迅與左翼〉中,運用美國學者契尼斯的「thos」一說,來解釋作為同路人魯迅身上「有所不忍」的獨特精神,與無情的革命左翼形成鮮明對比;那麼,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 「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精神氣質(ethos),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感覺,不忍看到他人受苦受難,並且認為人的尊嚴是互相聯繫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馬薩里克、哈威爾、海達內克這些非共人士,他們身上都有這種氣質,這使得他們之間能夠息息相通,一脈相承。而那些退而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前共產黨人比如姆林納日,儘管理想和個人生活遭到重大挫折,歷經磨難,但他們萬難不辭,寧願放棄個人利益,也要堅持信念,究其精神底色來說,也是這樣一種願意承擔他人苦難的倫理動機。實際上處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社會關係之中的不同人們,也給這種氣質帶去了自己的東西,令其更加豐富生動,包括馬克思主義者,也包括戰爭時期或者由戰爭造就的共產主義者。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捷克這片土壤,有過如此大面積社會主義力量的崛起。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78年,誕生於奧地利帝國時期,1918年建國之後,該黨在1920年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25.5%的優績;成立於1921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1925年的選舉中得票率有12.86%。直到二戰爆發之前,捷共的得票率一直在10%至13%之間。當然,這可以視為位於這個歐洲中心的國家,即使剛剛誕生不久,便有著成熟的議會民主制度,政治力量和思想十分多元。與包括蘇聯在內的蘇聯陣營其他國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完成現代性轉型的民主國家,在這裡,社會主義也不是誕生在貧瘠的土壤之中。布拉格作為一座擁有悠久歷史的歐洲文化名城,其思想之活躍、藝術之前衛,從18世紀起便令世人矚目。因為繼承了奧匈帝國的大部分工業設備,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上起步也比較高,至二戰之前,她已經躋身為歐洲工業四強,同時為世界第七大工業國(前六名為美、德、蘇、英、法、義),排在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前面。
捷克斯洛伐克戰前的總統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 1884-1948),本來是面向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但是「慕尼克協議」讓他和他的國家遭到西方世界的背叛,他不得不流亡多年。貝奈斯結束流亡回國途中經由莫斯科,而後組建了他的聯合政府。整個戰爭期間,當捷克國內其他勢力向納粹投降,主要是共產黨領導了地下抵抗運動,再加上被占領期間的悔恨屈辱,應該說戰後捷克斯洛伐克民眾對於共產黨的歡迎發自內心。1946年戰後第一次國民議會選舉,共產黨獲得了38%的選票,社會民主黨的選票位列第二,兩黨加在一起的席位超過半數,共產黨領導人哥特瓦爾德成為新政府的總理。1946年6月,共產黨的人數從1945年的5萬人上升到122萬人,到1948年1月達到131萬人,而全國人口為1200萬。19正如托尼.朱特所說,戰後歐洲各左翼政黨都因其戰時抵抗運動而收益頗豐。
應該指出,這個國家戰後國有化進程並非僅僅由共產黨所主導,而是與清算納粹有關。貝奈斯在流亡期間和戰爭結束後不久,便發布了一系列法令,包括銀行、保險公司、一些大型企業的國有化,沒收或低價出售納粹合作者的財產。因為以戰爭中的敵我陣營劃線,在落實這些法令時,基本沒有遇到社會的抵制。在迅速啟動經濟復甦(支援小企業和輕工業)的同時,哥特瓦爾德政府實行了免費醫療和教育,更是得到了社會的普遍歡迎。90年代在與戈巴契夫的對話中,回首當年,姆林納日稱這個時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激進變種」。「如果不是因為1948年2月試圖引入蘇維埃——也就是完全的史達林主義——制度,我們本來會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開始建立一個比後來從瑞典到奧地利的歐洲發展更為激進的福利國家的進程。」20
1948年的「二月政變」令事情發生了根本轉變。無論如何,政變之前,政府26名內閣成員中,只有9名共產黨人,其餘由非共黨派及兩名無黨人士擔任。為了反對共產黨內政部長的濫權,2月20日有12名非共部長以辭職提出抗議,在共產黨武力脅迫之下,貝奈斯接受了他們的辭職,空下來的部長位置立即被捷共的人所占據,貝奈斯也走到了他自己政治生涯乃至生命的盡頭。這之後,捷共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才得以確立,這個時間被認為是災難的開始。姆林納日的前妻麗塔.布迪諾瓦(Rita Budínová)說過一段話,代表了戰後成長起來一代人的思想過程:「我們在1948年都是20歲,那麼我們在1968年都是40歲。……我們曾經幫助國家陷入困境,所以,我們至少還可以幫助她走出困境。」 21「二月政變」時,麗塔和姆林納日這些年輕人都站到了共產黨一方,但這並不符合他們原先的理想和所處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文主義和民主的傳統。這位麗塔比姆林納日小一歲,跟隨父母在紐約度過了童年,1970年被開除出黨。「天鵝絨革命」期間,她是哈威爾的翻譯和新聞發言人,是她創造了「天鵝絨革命」這個詞。姆林納日曾給前妻家庭帶去了《七七憲章》影本,但是沒讓她簽,讓她父親簽了。她父親是一位老記者,1923年開始參加捷共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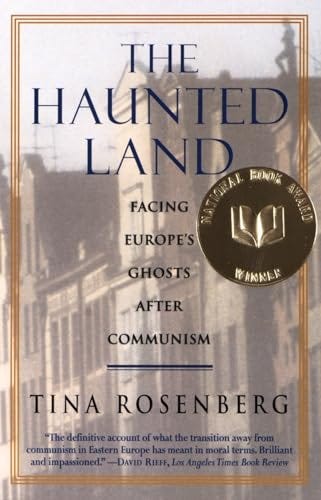
1968年的幫助國家「走出困境」是指什麼?這個國家當時想要往哪裡去?這年 7月在「布拉格之春」高潮中,有過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只有5%的捷克人說他們想要資本主義;89%的人希望繼續走 「人性化的社會主義 」之路。22而同時,有80%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正如歷史學家R. J. 克蘭普頓(Richard J. Crampton)寫道,捷共1868年4月釋出的「《行動綱領》所暗示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是將結合捷克的人文主義和寬容傳統,形成民主社會主義。」23 托尼.朱特也說:「認為他們追求『人性化的社會主義』的熱情僅僅是一種妥協論或習慣性的表達,這是錯誤的。當時存在的是『第三條道路』的想法, 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制度媲美, 它既尊重個人自由, 又尊重集體目標。」 24無論如何,短短八個月,捷克社會真切地沐浴在民主洗禮當中,各種聲音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工人、農民、學生、宗教界都發展出獨立團體和聲音,1948年被合併進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也打算在國民議會中重新尋求自己的代表。當時還有一個著名的無黨派人士俱樂部(KAN),突破了1948年以來的捷共框架,體現了政治多元化的民主要求。因出身一向謹慎的哈威爾3月份在《文學報》上發表政治文章,質疑「黨內民主」:「如果沒有全社會的民主,即使是黨內民主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續下去。不是後者保證了前者,而是恰恰相反:前者保證了後者。」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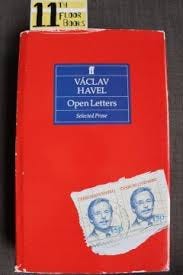
「布拉格之春」民主社會主義的高潮可以用這件事情來代表——這年6月26日,國民議會通過了《關於期刊和其他大眾媒體的法律修正案》,意味著正式廢除存在若干年的新聞和出版的審查制度,雖然早在2月份,當新的捷共領導恢復了此前被禁掉的《文學報》,審查制度這項共產政權的標配實際上已經不存在。而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民議會,能夠邁出這一步還是非同小可。雖然在《四月提綱》中仍然保留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但是不受審查的媒體已經將黨的領導撇在一邊,這正是「布拉格之春」中的張力所在。此時擔任國民議會主席的,是約瑟夫.斯姆爾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ý, 1911-1974)。他是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老黨員,在戰前議會民主時期,他擔任過布爾諾地區(捷克第二大城市)共產黨書記,他有一個弟弟自願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而犧牲。戰爭期間,斯姆爾科夫斯基是共產黨地下抵抗組織的領袖,1945年5月的布拉格起義,他是共產黨方面的主要領導人,後通過他的談判,達成了納粹部隊的投降協議,保住了這座美麗的城市。50年代初,斯姆爾科夫斯基受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事件」牽連,獲刑15年實際坐牢四年,1963年平反後,66年當選為捷共中央委員。當他68年4月當選為國民議會主席,從他本人政治生涯得出教訓,他與杜布切克一起堅定地推行社會民主的路線。1970年他被開除出黨後,很快成了被罷黜的前黨內改革派人士的核心。他沒有簽署《七七憲章》,實際上他1974年便去世了,官方擔心悼念會引發抗議,封鎖了他死亡的消息。他的骨灰盒一度被盜,後來在一列行駛的列車上被發現。
弗蘭蒂謝克.克里格爾(František Kriegel,1908-1979),本想在斯姆爾科夫斯基追悼會上致辭,但被官方拒絕。克里格爾的傳奇經歷,可以說是20世紀捷克斯洛伐克人道主義社會主義歷程的一個縮影,1968年8月他能在莫斯科拒絕簽署允許蘇軍駐紮協定和76年9月去法庭現場聲援搖滾青年絕不是偶然的。中文讀者對他也並不完全陌生,拙譯《哈威爾文集》中,有一篇哈威爾寫於1988年的回憶克里格爾(文集中翻譯為「克瑞傑」)的文章,哈威爾稱自己一直想能與克里格爾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想問問他:他為之獻出畢生心血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哪種社會主義更適合他?或者那只是與他早先的鬥爭有關、是證明他歷史的一個紀念品?1979年底哈威爾被收監期間還想著他,期盼等他出去能與他們夫婦見一面,但是同案的獄友告訴他,老先生已經去世了。同樣擔心悼念引發抗議,官方沒收了他的遺體,在一個寒冷的凌晨沒有告別儀式便直接火化。哈威爾分析他之所以不同於某些高大上的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是一名醫生,如同人們的鄰居一樣,畢生都在為具體的人們服務。
是的,作為醫生,克里格爾先生還為中國人民服務過,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柯里格」。他出生於建築工人家庭,年僅十歲父親去世,家庭陷入困頓,身為猶太人,他飽受歧視之苦。身處貧苦和面對不公,少年的克里格爾立志終身幫助窮苦的人們。母親含辛茹苦送他到布拉格查理大學學醫,他靠打各種零工——鞋匠的作坊、建築工地、群眾演員以及在足球場上賣香腸,用來維持學業。身處布拉格德語大學,身邊是腰帶上掛有納粹黨徽的亢奮同學,克里格爾選擇加入共產黨。1936年克里格爾參加國際縱隊赴西班牙作戰,他擔任醫生並獲得少校軍銜。他周圍的人們視他為罕見的、誠實和無私的人,能同時表現出兩種性格——勇氣和對他人意見的寬容。民主西班牙失敗之後,他是最後一批越過比利牛斯山脈撤退到法國的人之一,在邊境放下武器並將旗幟交給國際旅最高指揮部代表時,他留下了眼淚。
1939年初,法國用拘留營來歡迎這批冒生命危險的理想主義者。因戰爭爆發,他無法回到祖國,於是響應紅十字會的號召,參加了一支20人左右的醫療隊來到中國,其中有波蘭、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人,一位西班牙人也沒有,但因為是從西班牙戰場上撤退下來的國際志願者,中國人籠統地將他們稱之為「西班牙醫生」,每一個人都獲得一個中文名字。在香港準備進入中國之前,宋慶齡設宴招待了他們。其後這一行人繞道越南、經過廣西,抵達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駐地貴陽,他們每一個人都被任命為紅十字隊隊長,下面配備一個不太熟練的專職醫生,到部隊開設一個帶有手術室的醫院。他批評過中國的中醫。1941年,柯里格醫生隨中國遠征軍去到印度和緬甸,1943年在瓦魯班戰役(The Battle of Walawbum)中,柯里格醫生治療了約50個中國傷患。除了緊張戰鬥,還要克服蚊蟲和瘧疾,柯醫生一直堅持到戰爭結束。他本來是一名內科醫生,卻在創傷學、前線醫學和處理輸血積累了豐富經驗。1945年11月,他回到祖國繼續從醫,1949年被任命為政府衛生部副部長,1950年代遭到清洗。1960年,會說西班牙語的他還擔任過卡斯楚古巴共產黨政府的衛生顧問,幫助建立了古巴醫療保健系統,創辦醫學教育和醫學雜誌,以及推動接種小兒麻痺症疫苗。
1968年他重返領導崗位,4月份他當選為捷共主席團成員。除了黨內職務,柯里格醫生還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國民陣線主席。姆林納日曾設想以國民陣線來發揮不同政治黨派的作用,這正是柯里格醫生主政國民陣線時期,柯里格醫生同樣也是「布拉格之春」的風帆人物。在莫斯科他拒絕了簽署協定,蘇聯當局想扣留他,理由竟然是他父親是烏克蘭移民,而他的家鄉在戰後已經歸蘇聯管轄。但遭到了同行者們的堅決反對,直到最後一刻還爭論不休,最終他與大家一起返回。10月18日國民議會通過一項條約,關於蘇聯軍隊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駐留合法化,有228名代表舉手同意,10名投了棄權票,4名投了反對票,柯里格醫生是這四名國會議員之一。1969年5月30日,他在開除他的捷共中央委員會大會上的發言,是民間流傳的第一份Samizdat文本,他譴責這份俄捷協議不是用鋼筆寫的,而是用大炮和機關槍的力量寫就的。1977年,柯里格醫生成了第一批《七七憲章》簽署者。德高望重的他,無疑增添了《七七憲章》的份量和吸引力。
我找到了與柯里格醫生同時拒絕《莫斯科協議》的其他三名國會議員,他們其中有兩位與柯里格醫生年齡相仿,都是資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也都是《七七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其中有一名捷共中央委員:
1. 弗蘭蒂謝克.沃德斯洛(František Vodsloň, 1906-2002),1928年加入捷共,1940年曾因參加地下抵抗運動被判處過死刑,後關押多年。擔任過捷共農業黨書記(1948年)和捷克斯洛伐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1967),為捷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資深中央委員,1969年被開除黨籍。
2.格特魯達.塞卡尼諾瓦.查克托娃(Gertruda Sekaninová- Čakrtová, 1908-1986),早年做過律師,1932年成為捷共黨員,與1943年被納粹處決的共產主義者、記者伏契克是朋友,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死於納粹監獄。戰後這位傑出的女性曾任捷克外交部副部長和駐聯合國大使。經歷了政治山的跌落(1957年)之後,擔任過全國婦聯副主席,1968年積極參與了《行動綱領》的制定和廢除審查制度,1969年被開除出黨。她不僅是《七七憲章》首批簽署者,而且還是1979年哈威爾等人創建的「保衛受不公正審判的人的委員會」(VONS)創始人之一。
七七憲章的首批簽署者中有三位醫生,除了柯里格醫生,其餘兩位先後都是捷共中央委員:
1.弗蘭蒂謝克.布拉哈( František Bláha, 1896-1979),他是我看到的最年長的《七七憲章》簽署者,曾因參加地下抵抗運動,被關在達豪集中營六年(1939-1945),戰後是社會民主黨主席團成員,1946年的第一次大選,時任社會民主黨身分的國會議員。1948年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併,他被選為合併之後的捷共中央委員。曾任布拉格總醫院院長,1968年在復興進程的餘音中,捷克和斯洛伐克改為聯邦關係,布拉哈醫生擔任聯邦議員,但很快從這裡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2. 伊日娜.澤連科娃 (Jiřina Zelenková 1929-1988),她是首批簽署者中三位醫生之一,捷共十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因反對入侵被開除黨籍遭到懲處之後,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於1979年找到一份在精神病院的工作,最後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在首批簽署者中,我還找到了這樣一些捷共中央委員:
1. 盧德米拉.揚科夫科娃(Ludmila Jankovcová, 1897-1990),同為資深社會民主黨人。1948年時這位女性是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兩黨合併之後從1948年到1969年她始終是捷共中央委員,她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第一位擔任部長的女性,先後擔任過工業部長和食品部長以及副總理,多次獲得共和國勳章。因積極參與68年的復興進程,1970年被開除黨籍。
2. 弗拉基米爾.卡德萊茨(Vladimír Kadlec, 1912-1998)經濟學家,擔任過布拉格經濟大學的校長,1968年時任政府的教育部長,捷共十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捷共中央後來批他稱他為「右翼代表」,畢竟經濟學家更容易獲得「右翼」稱號。
3. 溫涅克.希爾漢(Věněk Šilhán, 1927-2009),經濟學家,是半秘密的十四大的領導人,並在該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4. 博胡米爾.西蒙(Bohumil Šimon, 1920-2003)經濟學家,1968年時政府的經濟部長,他不僅是中央委員,還是中央主席團成員,與姆林納日一樣,都與杜布切克一起被綁架到莫斯科,在可恥的《莫斯科協議》上簽了字。1969年西蒙被開除黨籍。
這麼算起來,連同柯里格醫生,《七七憲章》首批簽署者中有三名前主席團成員,換個說法即中央政治局委員。這3人加上我們剛剛提到的五位和下面將要提到的兩位:胡布林和薩巴塔,再加上外交部長哈耶克,一共有11位捷共中央委員(僅指68年在任的)。首批簽署者裡還有布拉格市委書記拉迪斯拉夫.利斯(Ladislav Lis, 1926-2000,曾擔任過「七七憲章」發言人),這真是一個漂亮的紀錄。
如此說,不是仰望權力。說到底,政治是要有脈絡和代表性的,這些人的立場、身分在社會中的能見度,給出了這個社會本身的深沉脈絡和願景。當他們簽署憲章時,他們知道,這是把他們打入賤民階層的入口,但會令他們的信念和人格得到刷新。捷共官方在公開媒體上稱他們為「破產的和被黨排除在外的政治家」,把柯里格醫生稱之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爪牙」。還有一位簽署者,官方稱他是「資產階級前政治代表」,這便是普羅科普.德蒂納(Prokop Drtina, 1900-1980),律師出身,於1945年到1948年任司法部長。「二月政變」時,他是以辭職提出抗議的12位部長之一。有說姆林納日於1976年底特地前往布拉提斯拉瓦找杜布切克(他是斯洛伐克人),希望他能夠簽名,但只見到了他的司機。
哈威爾於1988年1月「天鵝絨革命」之前寫給柯里格醫生的這段話,給出了對於這些一輩子為了理想而獻身人們的最好理解和致辭: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在這個國家,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政治家——他們是正直的、忠誠的和不屈不撓的人們,儘管其命運通常是悲劇性的。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已經很難想像這種事情,因為他們所知道的國家領導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義者,說著僵屍般的語言,他們坐在開得飛快的轎車裡駛過大街,或偶爾在電視裡念那種承擔缺少真實生活的冗長乏味的陳詞濫調。值得為弗蘭蒂謝克.克里格爾寫一本真實、令人信服的書。這不僅是保留一個傑出人物的記憶,也是讓年輕一代對這個複雜的世界有很好的理解,對他們的前輩為什麼做這麼多有更好的理解,知道更多關於他們的問題、理想、想像、成就和失敗。這或許能幫助並最終可以讓他們意識到,政治和政治家並不是必然被嘲笑的對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對象。26
寫一本關於柯里格醫生的書,哈威爾的這個願望已經達成。作者是捷克導演伊萬.菲拉 (Ivan Fila),他最初寫的是電影劇本,但是後來因各種原因沒有拍成,這本傳記的名字叫做《擋道者》。2023年,又有了一本柯里格醫生600頁的新傳記面世,作者是1976年生的馬丁.格羅曼(Martin Groman)。書的背面運用了柯里格醫生在自己日記中的一句話:「我這一生是在追逐海市蜃樓嗎?」這位作者認為,「社會主義」對於柯里格醫生來說,是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同義詞。
其實中國倒是應該有一部關於柯里格醫生和他的西班牙同行的電影。
姆林納日解釋「持異議者」現象,也經常被人們引用。在他看來,雖然這些人們被打壓,但還是構成了在這個制度之內的合法性存在,這是60年代之後才出現。在典型的史達林時期,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存在,而是一律斬草除根,直接槍斃或送去勞改,完全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而這之後,官方則採取了選擇性鎮壓的措施,並不把每一個不信任的對象都抓起來,而是選擇他們中的一些人加以處罰,目的在於殺一儆百。那麼,作為制度之內的合法性壓力集團,新挑戰者就要儘量利用現有制度框架,要求權力在實踐中履行它所宣稱的,讓權力做到他自己所承諾的,針對他們自以為高明的地方加以戳穿。在姆林納日看來,這是比制定新的改革方案和行動更加激進的政治行為。它可以不停地重啟矛盾,暴露極權主義想要掩蓋的本質。這是一個「持異見者」本人往往不願意承認的事實,雖然遭到各種騷擾,但他們實際上是這個社會中合法性或準合法性的存在。如何最大限度地運用這種條件,是一種政治智慧。
放到坦克鎮壓之後的環境中去,經過轟轟烈烈的「布拉格之春」,官方的確無法想像能夠對全部反對他們的人趕盡殺絕。1970年底整肅完畢、重新登記黨員時,捷共失去了50萬名黨員,包括被開除的和自動離去的,占原先人數的三分之一。許多人失業和離開原先的工作,一下子跌落到普通民眾當中,成了「正常化」開始之後反對力量的潛在基礎。當然,與整個社會一樣,在以消費為藉口的維穩秩序中,一般人們更多採取的是口是心非的方式,但是仍然有一批人不屈不撓地站了出來。在沒有接觸他們這個群體之前,我相信過一個流行的說法,即一直到了「七七憲章」,人們才甩掉了思想上、精神上的負擔,有重新挺起腰桿做人的感覺,但其實不然。
有一批人從來沒有屈服過,而是以各種形式、運用自己的條件進行抵抗,公開乃至激烈地挑戰胡薩克當局,在政治光譜中他們始終屬於左翼一邊。他們當中有人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他們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有人加入過共產黨,但是告別了共產黨員的過去;也有人沒有告別共產黨員的過去,也許潛意識裡並沒有完全放棄共產黨領導作用,但出於自身的社會責任感,一樣給胡薩克當局出大難題。正是他們在所謂「正常化」的政治霧霾天空,最先打出民主反對派的旗幟,產生和積累起最早的反對能量。這股能量又傳導幫助促成了「七七憲章」。這批人繼而又成為「七七憲章」中的活躍人士、主力和骨幹。
為了形成更廣泛的反對共識,他們甚至淡化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做出了某種犧牲;然而在80年代後期,臨近「天鵝絨」轉型前夕,又是他們率先提出政治要求,超過「反政治的政治」,組建不同的政治平臺或團體。這些人當中也有人反覆坐牢,判處的刑期更重,加起來刑期比哈威爾還長。
「社會主義反對派」是這些人的自我命名。這個概念的公開出現是在1971年1月到2月期間起草的一份叫做《社會主義反對派短期綱領》中,它是「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二份文件。兩個月前,即1970年10月28日,在布拉格、布爾諾等地出現了一份叫做〈十月二十八日宣言〉的傳單,便是這個「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的起始。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社會主義」——在被坦克碾碎之後人們能夠找到的共同語言和身分標誌——保留了「布拉格之春」時改革的共產黨人一個成果,即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理想相結合;由「公民」這個詞所釋放和強調的,主要是法律意義上平等的個人身分和權利。
就成員來說,「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由全國各地因反抗被打壓的不同人群鬆散組成,以印刷傳單、張貼海報的形式不斷出現在人們面前,還擁有一份名為《政治月刊》的Samizdat刊物,自1971年1月起每月定期出版。在其先後發布的近百份文件中,也有一些發布在布拉格工廠裡工人自己出版的刊物上面。他們自稱該運動有三個層次:幾千人組成的「倡議團體」(發聲者);由幾萬人組成的「潛在領導政治階層」;以及由幾十萬人組成的「成員基礎」。27運動的領導人自始自終沒有走到前臺來,但是許多人都知道,官方更不例外,最後實行抓捕,獲刑最重的便是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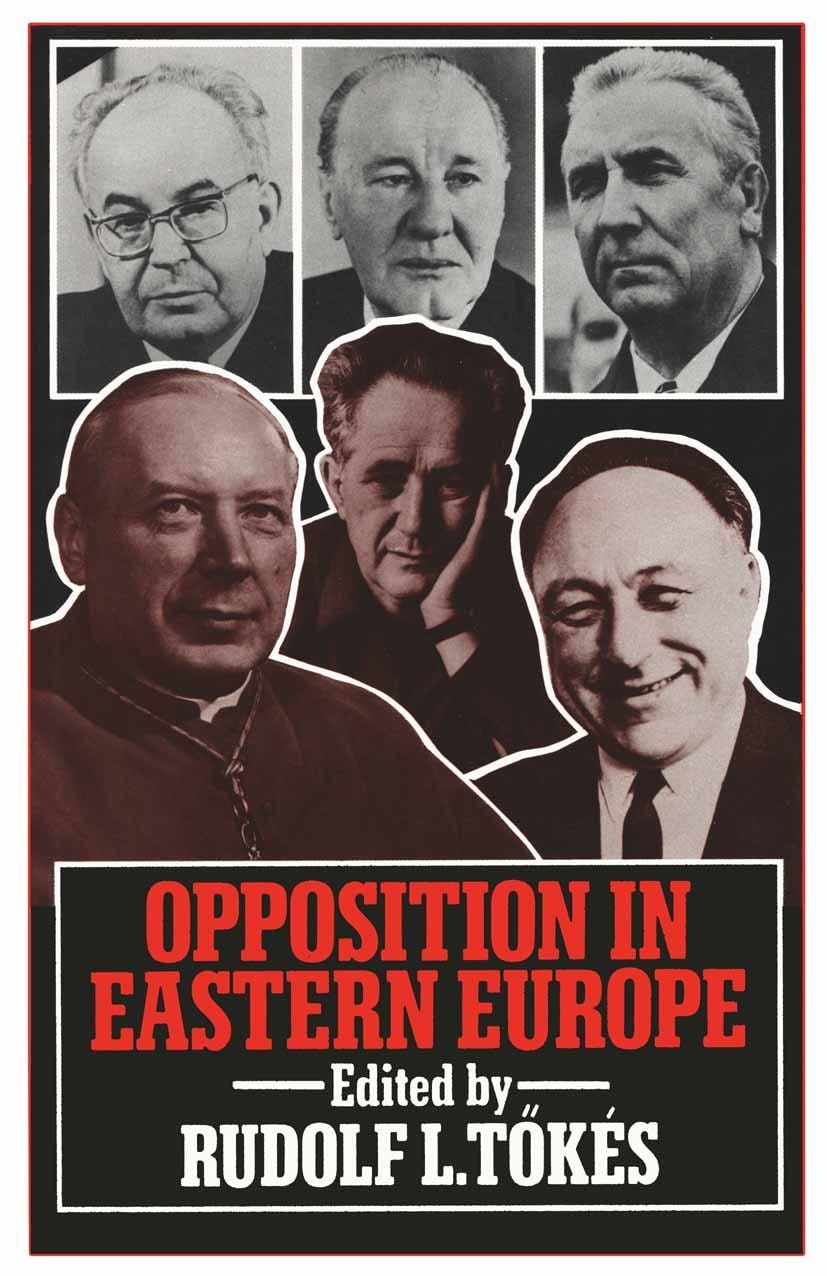
第一份宣言從標題上便解釋了10月28日這個時間的重要性,也是給出了他們這個運動的合法性,它秉承了這樣三個傳統:一、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結束了三百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二、1945 年 10 月 28 日,流亡歸來的愛德華.貝奈斯政府頒布法令,將重工業、採礦業、大宗土地和銀行國有化,從而奠定了社會主義秩序的基礎;三、1968年10月28日,杜布切克政府宣布共和國聯邦化,給予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平等的地位,實際上是給予斯洛伐克人平等民族的地位。
這份面向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呼籲書,聚焦在呼籲允許捷克斯洛伐克「找到自己發展和進步的道路和方法」,從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的、獨立的和自由的國家,並完全擁有自己的主權」。在談到「國有化」時,宣言中寫道:「我國工業的國有化是我國歷史上解放的重要一步。但後來發現,國有化的財產並不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家機器。它不是工人的財產,而是國家官僚的財產;它不是用來資助人民的政府,而是官僚政權。」28在批評蘇式共產政權時,該宣言主要運用「官僚機器」、「官僚結構」這樣的提法。這是包括這份文件在內的東歐社會主義反對派讓西方左翼感到不滿足的地方,覺得他們在理論上沒有創新,沒有提供一套新的工人階級解放的目標和鬥爭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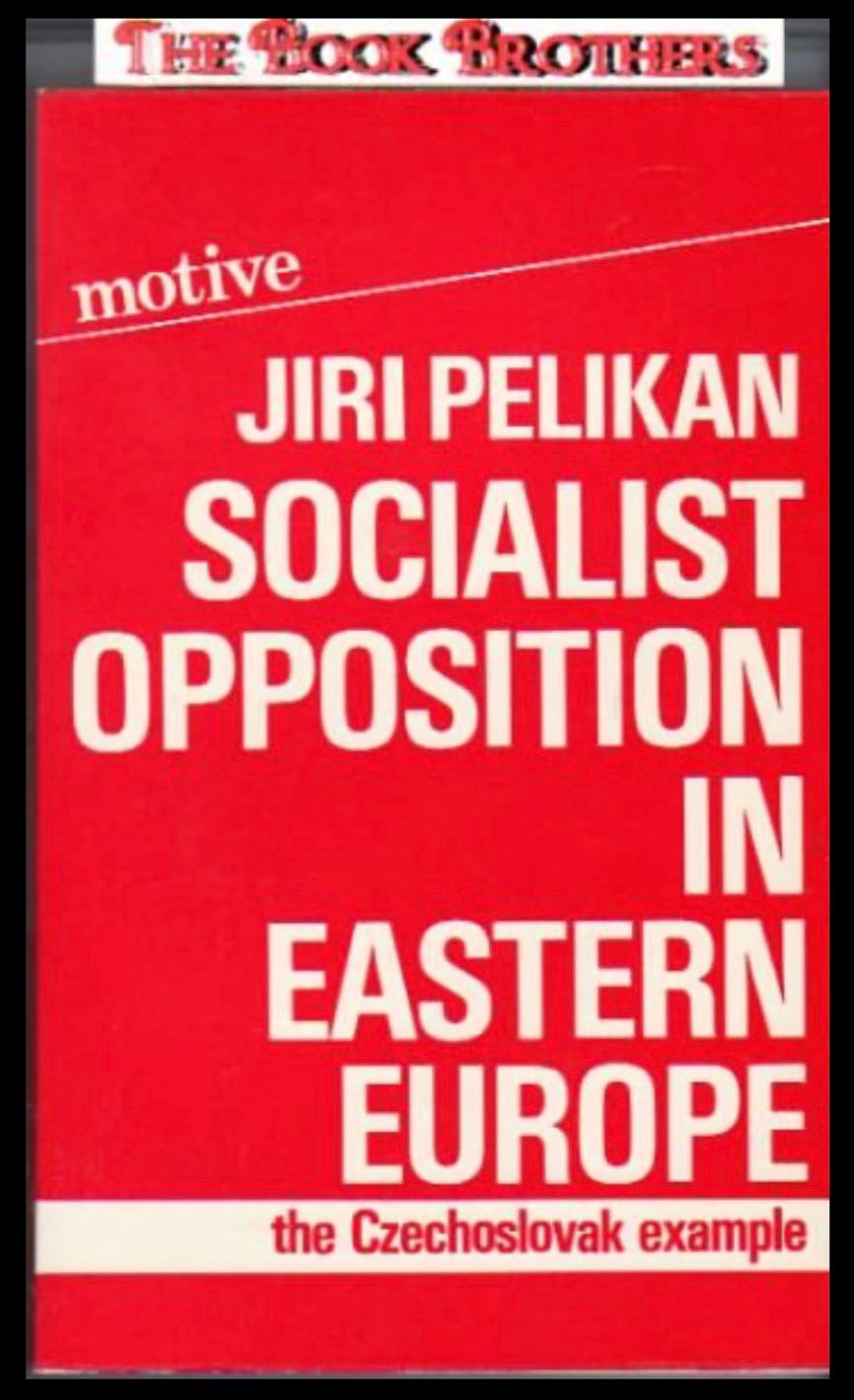
第二份以「社會主義反對派」自居的文件雖然用到了「短期綱領」的字眼,其篇幅並不短,是一份呼籲全面改革的新方案,實際上是一個討論文本,直到大抓捕之後,才出現在流亡義大利的反對派雜誌《信報》(Listy)上面,我們在下面還會提到這個雜誌。稱之為「綱領」,是要與1968年姆林納日參與弄出的捷共《行動綱領》遙相呼應,但是在其具體表述方面,這份文件的當事人認為自己「繼續前進」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其中超出當年的部分有:第一,以「民主社會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民主」,並指出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只需要深化、發展和完善(現有體制);而我們所關注的是一種需要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結構性)變革的制度」。第二,進一步的抵抗和變革應該面向社會而非國家,從而強調政治多元化而呼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一點被官方抓住猛批不已。第三,在「鬥爭路徑」方面,不再相信此前僅僅是從上而下的改革路線;認為除了從內部和從上面開始的形式,強調還有「從下面」(from below)和「從外面」(from outside)施加壓力,以及從內部和外部、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結合。文件中提到官方用「右派」來稱呼他們,但他們認為這只是出於官方的宗派教條主義,他們自己從來不接受這個說法。
1971年秋,「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發起了自68年以來最為令人矚目的活動。針對胡薩克政權想要控制在11月份舉行的國家領導人選舉,「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發布了一份「選舉呼籲」來加以抵制,在9月到11月選舉期間,該運動成員在布拉格、布爾諾和全國的其他城鎮張貼和散發傳單,大聲疾呼眼下選舉不是真實的,因為選舉的結果早已經由黨的領導層決定,贊成票的比例已經下發給基層選舉委員會。呼籲書號召人們要麼棄權,要麼劃掉已經指定好了的唯一候選人。這份呼籲書也得到了其他反對派團體的簽署,包括以抗議蘇軍入侵而自焚的學生來命名的「揚.帕拉赫革命小組」、「公民抵抗運動」(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部)以及「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在後來的中央委員會上,胡薩克聲稱有10萬份傳單,估計員警沒收了一半多。
大抓捕很快來臨,短短幾個月內,被抓捕的人之多和判刑之重,達到了胡薩克時期的頂峰,甚至比後來對付「七七憲章」還要嚴厲得多。前後大約有200人被捕,有47人被判處刑期總共加起來118年。這之後,公民社會主義運動又繼續發表了六、七十份文件,但因主要成員都被抓進去,這個運動漸趨沉寂。這個運動縮短了原先在人們當中明顯存在的「黨員和非黨員」的距離。
官方審判結果出來之後,進一步證實了人們對於其領導人的推測。米蘭.胡布林(Milan Hübl, 1927-1989)和雅羅斯拉夫.薩巴塔(Jaroslav Šabata, 1927-2012)被判刑最重,兩人均被判處六年半刑期,他倆同樣也是68年8月危機中召開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新選出來的中央委員。胡布林此前在大學任教和在社科院擔任研究員,研究工人、社會主義運動及民族問題,1968年改革浪潮中升任中央黨校校長,他也被認為是第一位開始研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關係的捷克戰後歷史學家,深知解決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關係是全國改革運動成功的關鍵,他參與推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化和起草聯邦法律。因主張改革和反對入侵,1970年的整肅運動中他被黨開除和剝奪一切職務。1972年的審判中,他的罪名是試圖顛覆國家政權。被判重刑的若干人於1976年12月10日人權日提前釋放,剛出獄的胡布林成了《七七憲章》的首批簽署者。這位胡布林也被經常用來說明胡薩克這個人權迷心竅。他與胡薩克同為斯洛伐克人,50年代初胡薩克遭到整肅時,胡布林一直是他的支持者,後來也積極支持胡薩克復出。但缺乏信念的胡薩克翻臉不認人,把老友送進監獄判以重刑。共產黨的歷史教授胡布林最終倒在了黎明之前,他於1989年10月28在布拉格病逝。
薩巴塔原為大學馬克思主義及心理學教授,最早傳播社會民主的思想。在捷共《四月提綱》出臺之前,他就在電視上說必須由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來統治。共產黨並不代表所有公民,在許多層面上公民應該有自己的民選代表,這些改革派言論,使得他在布爾諾地區擔任黨的書記。1969年,他被解除所有職務後,做過混凝土工人和倉庫工人,1971年被開除黨籍。他是一位告別了自己共產黨過去的社會主義者,70年代初便稱自己已經「不是改革的共產黨人,但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不相信這個黨能夠從內部變革從而實現自我更新。1973年末,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戈利安即將抵達布拉格,獄中的薩巴塔給這位譴責蘇軍入侵的英國共產黨領導人寫了一封信,提醒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他們不是反國家的,而是左派意義上的反對派。他想說明在這個國家真正的左派沒有投降,而是被關在牢裡。他轉而又給胡薩克了寫了一封信,說「如果反對派不是反社會主義者(與法院的判決不同),不是被壓制,而是被視為對話夥伴,這對國家及其聲譽不是更好嗎?」他的這兩封信從獄中被帶出來「走私」發表在境外雜誌上,他接著被控告「在國外損害共和國利益」,六個月之後又撤銷了罪名。他與胡布林同一天(12月10日)被提前假釋,不顧「帶罪之身」,他出席了「七七憲章」的第三次討論會(12月20日),不僅簽署了憲章還幫助尋找簽名。1978年4月份,在前外長哈耶克擔任憲章發言人一年多之後,薩巴塔接替了哈耶克,被放在憲章中前共產黨人的脈絡之中。不知道為什麼,1978年4月薩巴塔擔任「七七憲章」發言人,中國的《參考消息》上面還轉載了來自「法新社」的這個消息。29 順便地說,自「七七憲章」事件之後,中國的《人民日報》有零星的轉發外媒有關《七七憲章》的消息,主要是當作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正面範例。
幾個月(1978年8月)之後,薩巴塔與哈威爾等人想要在捷波邊境會見波蘭民主的反對派,遭到阻止之後,薩巴塔揮拳打了員警一個耳光,接下來又被判刑兩年。他第二次被捕在法庭上堅定微笑的光輝形象,由女兒安娜和一名女記者文字記錄下來,通過地下刊物流傳之後,一時令人士氣大振。不過人們也在同一份刊物上討論過為了這一巴掌而坐牢到底值不值。薩巴塔這個人的特點是牢獄之災絲毫沒有減弱他的鬥志,反而越戰越猛,在憲章中他是一個激進派,他始終反對《七七憲章》「反政治的政治」的提法,認為「七七憲章」本身就是政治,是一個潛在的政治結構或組織,用他的話來說,他始終想「把憲章馬克思主義化」。
作為「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二號人物,薩巴塔幾乎把他全家都搭進去了。在他被捕之前,員警已經抓走了他的兩位兒子瓦茨拉夫、揚和女兒安娜,此時安娜才21歲。年輕人被判監禁6個月到兩年不等。這些人的罪名與哲學家海達內克一樣——散發傳單、破壞選舉。當然,薩巴塔家的年輕人也都加入了「七七憲章」,女兒安娜是憲章需要三個發言人的提議者,她的提議在第一時間得到採納。安娜被判入獄之後,在獄中與父兄一道認識了佩蒂.烏爾,此時的烏爾在另外一個案子中已經蹲監三年,一對年輕人在1973年先後出獄之後結婚。
佩蒂.烏爾,是「七七憲章」中最年輕的創始成員,而且自始至終是最為活躍的人士。烏爾年輕時在大學裡學機械,他有一位老師伊日.赫爾馬赫(Jiří Hermach, 1912-2011),這位馬克思主義教授1968年參與了杜布切克「社會主義新概念」的團隊,該團隊旨在發展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在8月入侵前幾天完成了其工作報告。烏爾深受這位老師的影響。1967年夏天烏爾還去了一趟巴黎,結識了那裡的托派馬克思主義者,因此烏爾的思想帶有托派色彩,主張工人自治、實現所有權的公平管理、最終廢除國家。烏爾從巴黎還帶回來波蘭激進左翼活動家雅切克.庫隆(Jacek Kuron)和卡洛爾.莫澤列萊斯基(Karol Modzelewski)頗具爭議的〈致黨的公開信〉,與朋友一起翻譯出來加以傳播。雖然是一名激進左翼,但這位烏爾從年輕時起便拒絕加入捷共,與他後來的岳父一樣,認為這個黨無法從內部得到改革。烏爾的最大特色是行動力極強,先後組織和參與過一系列激進的政治活動。1968年6月至8月,他參與組織了一個叫做「左翼立場協會」的俱樂部。蘇軍入侵之後,他又與友人聯合組創了「革命青年運動」團體,其成員為查理大學的哲學院、生命學院學生及這所大學的畢業生。該運動以「革命社會主義黨」的名義,四處散發反對胡薩克政權的傳單,他們與布拉格印刷廠的工人建立聯繫,列印了20萬份傳單,除了張貼之外,還在鐵路工人的幫助下從火車上扔了下來。在紀念占領一周年的抗議活動中,這個團體的年輕人積極走向街頭,雖然點燃警車和推翻電車不一定是其成員們的作品,但符合這些人的激進理念。1969年年底這個團體有19人被捕,罪名是「反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政策」。一年多的調查之後,烏爾和他的朋友們在1971年3月被判刑,烏爾的刑期最重,被判4年。同時被判入獄的年輕人中,後來至少有5位成了《七七憲章》第一批簽署者,烏爾的馬克思主義者老師赫爾馬赫也是首批簽署者。
從《七七憲章》發布的第二個月,烏爾開始向世界定期公布《七七憲章》簽署者遭到衝擊的情況。到這年10月,烏爾共寫了8份這樣的報告。在這個基礎上,1978年1月烏爾創辦了《七七憲章資訊》(Informace o Chartě 77,簡稱Infoch),它迅速發展為一個有關簽署者的新聞事件及各種問題、理論探討的交流中心,成為「七七憲章」非官方的官方平臺,當然是Samizdat的形式。最初三期是匿名的,從第四期開始,烏爾在每期的首頁目錄下面增加了一個說明——「由《七七憲章》的獨立編輯小組出版」,後面是他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這個獨立編輯小組主要成員其實只有烏爾夫婦。該刊原則上每月一期,每年實際出版10到12期。1979年下半年烏爾再次入獄,因為與哈威爾等人共同創辦「保衛受不公正審判的人們委員會」(VONS),該團體的創辦者都是「七七憲章」成員,但又是獨立於「七七憲章」,為自己的行為單獨承擔責任。捷共當局避開了直接鎮壓「七七憲章」,那畢竟是他們自己法律通過的內容,但是對於這個組織毫不手軟,哈威爾被判四年半,烏爾被判五年,其餘四人被判兩年到四年。
但即使是烏爾入獄,《七七憲章資訊》也沒有中斷過,他妻子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封面上,地址不變。1978年至1989 年間,《七七憲章資訊》共出版了 189 期,共計發表了4,120 篇長短不一、風格迥異的文章。除了報導人權衛士們受到各種騷擾和壓制的報導及採訪,還有良心犯家屬對於親人的深情回憶和她們的生活報導,哲學家海內達克與一位年輕人的通信——他建議年輕人不要簽署《七七憲章》,憲章並不招兵買馬,比簽署重要的是根據憲章的精神去生活,這些內容都發表在這份刊物上面,它把憲章辦成一個生動活潑的生活社區,而不是整天板著臉孔的地方。有一份資料顯示,當年這份 《七七憲章資訊》1988年底10期到22期可以郵購,每份包括郵費在內的費用為10克朗。
作為憲章成員,在憲章之內烏爾保留了自己的立場。1982年他坐牢期間,在西方的流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書《社會自治綱領》(與人合作)。與他「民主的和自治社會主義」立場比較接近的是他的老丈人薩巴塔。烏爾雖然與哈威爾並肩作戰多年,但與哈威爾有過許多爭論。當哈威爾說「女權主義瘋了」這樣的話時,被烏爾抓住加以痛扁。1989年春天,烏爾發起組建了「左翼選擇」(Left Alternative),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導向、追求民主和自治的激進政治團體。「天鵝絨革命」之後,烏爾成為聯邦議會議員(1990-1992),後來加入了綠黨,一度成為綠黨領袖候選人。差不多有十餘年,他擔任捷克政府和聯合國的人權官員,為困境中的弱者說話,那是他一輩子的宗旨。他反對哈威爾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戰爭中的立場,批評哈威爾在靠攏美國時偏離了歐洲的價值。他沒有出席哈威爾的葬禮,因為葬禮是在布拉格聖維特大教堂內舉行,他說哈威爾從來不是基督徒。
因傳單事件引起的大抓捕而入獄,還有三人:巴泰克(Rudolf Battěk, 1924-2013)、揚.特薩(Jan Tesař, 1933-)、和伊日.穆勒(Jiří Müller, 1943-) 。他們立場和旨趣比較接近,是68年湧現出來、生活在布爾諾的優異人物,也都是《七七憲章》的首批簽署者。這三人出獄之後,於1978年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平行團體——「獨立社會主義」。
巴泰克是這個團體的領袖。這位巴泰克也是我特別尊敬的人士,他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卻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薩巴塔在某處說過哈威爾這些1936年生的人,在戰後成長起來,因此「與共產主義沒有糾纏不清的關係」,但巴泰克是1924年生,他也不追隨共產黨,但其頑強不屈、百折不撓,顯然又屬於戰前成長起來的那一代。60年代,巴泰克曾在捷克社科院擔任研究員,1968年4月,他參與發起了一個「無黨派人士俱樂部」(KAN),並擔任副主席,這個組織匯聚了對政治感興趣卻不在任何黨內的人,從而深受歡迎,一時名聲大振,但在能夠獲得官方正式登記之前,坦克便開進來了。1969年底,他與特薩走到一起,抗議蘇軍入侵並試圖組建獨立工會,作為未來的抵抗平臺。結果兩人同時被捕,被關押了13個月,未經審判而釋放。
特薩是一個歷史學家,主要研究納粹占領時期的地下抵抗歷史,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名「道德社會主義」,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與右翼相結合的某個品種。在對西班牙轉型的研究中,特薩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概念。他對烏爾的「激進自治」概念不感興趣,認為那樣會帶來破壞性,但是這並不影響特薩與巴泰克一道尋求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聯結。1969年春天特薩主動退黨,徹底拋棄了自己共產主義的過去。當他和巴泰克一起投入「公民社會主義運動」散發傳單,其實是剛出獄不久,加上此前的各種「案底」,特薩這回被判6年,巴泰克被判3年。1978年他倆同時也是「保衛受不公正審判的人委員會」(VONS)的發起人。關於反對派和反對運動,特薩特別強調不要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裡,而要關注整個社會的看法及自身與社會的關係。1979年秋,特薩與哈威爾等人同時被捕,第二年特薩接受了流亡。巴泰克稍後(1980年)再次獲刑5年。「三進宮」加起來,這位巴泰克實實在在蹲監時間前後共有10年之久。
穆勒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也沒有加入過共產黨。1966年他因為想要在黨的領導之外從事學生運動而被開除,1968年獲得平反重返校園時,穆勒是一個令人矚目的青年領袖。他發起了一系列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活動,組建「工人/學生行動委員會」,促進工人自我管理的專案,是一名旗幟鮮明的非共社會主義者。1970年春,他再次被大學開除,這次他被判五年半。他年輕勇敢,在審訊期間及獄中受到了暴力對待,在法庭上大聲為自己辯護的聲音被人們廣為傳誦:「我的活動不是反社會主義,我的活動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立場之上的。」薩巴塔回憶說,1976年耶誕節剛過,是穆勒向他介紹了《七七憲章》,穆勒與他一起組織了布爾諾地區的簽名。
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都是想堅持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是中歐社會主義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更像自19世紀以來歐洲傳統社會主義者。這個「獨立社會主義」團體,令人矚目的起點是發表了一份〈捷克社會主義百年宣言〉,其中恭敬地評論了1948年「二月政變」之前的捷克社會主義傳統。〈宣言〉回顧了100年前在奧地利成立的捷克社會民主黨定下的理念,對比當時提出的反對勞動資料的壟斷、選舉權、新聞和結社自由、消除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指出今天的現實與當時的理想距離更遠,哪怕是「七七憲章」,也只能在最高立法機構批准的法律框架下進行,而不能言及公開組織這樣的事情,工人階級也沒法自己組織起來。這份宣言最初發表時有23人簽字,巴泰克名列第一,哈威爾的名字被放在第二位,除了特薩、穆勒,還有反法西斯老戰士柯里格醫生、哲學家拉迪斯拉夫.海達內克。薩巴塔和烏爾翁婿後來都對這份宣言表示了口頭支持,但他們不在名單上。烏爾後來說,如果找到他,他也會簽的。但顯然,在獨立社會主義者們看來,他們的立場與烏爾的革命社會主義還是有差距的。
然而不管他們如何定位自己,這些社會主義反對派——也包括下面所要談到的前改革派共產黨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突出強調他們的立場是政治性的,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屬於政治活動的範圍,具有政治性質,因此一概反對「反政治的政治」,儘管在「七七憲章」的內部,或作為《七七憲章》的文件及共同發聲時,「七七憲章」仍然主要保持了意識形態中立的路線。但批評的聲音始終伴隨。1987年,40個年輕的簽署者共同發起一份致「七七憲章」的公開信,批評其非政治的策略。1988年下半年開始,其他獨立團體的活動也在增加,人們又開始躍躍欲試走向街頭。
1988年10月份,巴泰克和瓦茨拉夫.本達(Václav Benda,天主教徒,資深反對派人士,「平行城邦」的提出者)發起「公民自由運動」(HOS),在其宣言《為所有人的民主》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涉足政治的時候到了」:「必須恢復政治作為一個活動領域。它必須再次成為表達和推進社會真正利益的焦點。」這可以看作人們對此時的「七七憲章」無法滿足更大的政治活動需求的反應。宣言包括民主、政治多元化、經濟繁榮、保護環境、信仰自由、獨立工會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歐洲」等12項訴求,廢除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再次被明確提出來。薩巴塔也是推進這個運動的主要人物,海內達克和哈威爾都在名單上。烏爾沒有簽這個,他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是自1948年之後,第一份由反對派制定的具體的政治綱領,因此HOS實際上已經變成當時執政共產黨的第一個政治對手,同時也表明本來是多元化的「七七憲章」內部,開始公開分化。一些此前沒有加入「七七憲章」的人,尤其是那些立場略微偏右的人們,紛紛加入到HOS中來。
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的大學生上街遊行,紀念50年前被被納粹殺害的學生揚.奧普勒塔爾(Jan Opletal, 1914-1939),遭到員警鎮壓,學生們決定罷課一周並向全國各界發出呼籲,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或稱「十一月革命」)的引爆點。為了響應學生的號召和全國已經點燃的革命熱情,兩天之後即11月19日,「公民論壇」(OF)成立。這是一個由多方力量組成的政治聯盟,主要擔當了與捷共政府的談判,將權力從獨裁的一黨專制過渡到民主政治,哈威爾擔任「公民論壇」的第一屆主席。搭建「公民論壇」有著許多不同的政治力量,其中有好幾個是從「七七憲章」分化出去的獨立團體:哈威爾代表「七七憲章」、巴泰克代表「公民自由運動」,烏爾代表「左翼選擇」,還有比如年輕人創辦的「獨立和平協會」(IPA),以民間的名義宣導世界和平,其領導人露絲.索爾莫娃(Ruth Šormová)1965年生,1988年的《七七憲章》簽署者。
組建「公民論壇」的不同政治力量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團體是「社會主義復興聯盟」(Obroda),正式成立於1989年2月,醞釀的時間要更早。這個組織名稱當中的「復興」,點明了其宗旨和成員與1968年的「復興進程」相呼應。其17個創始會員,有一半簽過《七七憲章》,包括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原捷共中央委員。到80年代中期之後,他們覺得《七七憲章》已經不能滿足自己的政治要求,不能繼續停留在其「反政治」的框架之內。在新的條件之下,需要公開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在當年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的版圖中,這些人始終處於他們自己的一側。
無論如何,這些人曾經身處共產黨的深深庭院,雖然因為自己的選擇而跌落出來,但他們仍然有著自身經歷中形成的邏輯和行為方式。長期的共產黨的紀律約束以及個人生活範圍,使得他們並不能作為個人直接面對社會,像姆林納日和柯里格醫生那樣,直接走到普通人們中間;也不排除他們當中,有人仍然有意識或無意識相信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輕視社會力量。反正,當他們不在黨內時,他們也更願意待在自己人之間。1970年胡薩克完成黨內肅清,這些被驅逐的改革的共產黨人,很快聚集在原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周圍,其中有約20名前捷共中央委員。他們有家庭場所的定期聚會(「週三沙龍」),討論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問題,互相之間走動而少與外界來往,思想和行動趨於一致,這就是姆林納日為什麼在短時間之內能找到那麼多黨員簽署者。「七七憲章」三位發言人之一的前共產黨人代表,也從這個群體中產生。
他們反對蘇聯入侵有獨立國家的考慮,但是更主要的是,坦克碾碎了他們民主改革的理想,他們視自己為「布拉格之春」遺產的繼承人。一方面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胡薩克當局推行的「現實的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認為這不過是維護現狀、拒絕批評和變革的擋箭牌;而另一方面,他們仍然期待有機會完成68年未竟的事業,再來一次從黨內開始的改革,走出一條自身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很難改變思路還有一個具體原因,即他們原先改革的話語,只能在體制內得到實現,目前他們身處體制之外,但這套表述並不能直接轉化為反對派話語。他們被「去制度化」之後,只剩下一個公民身分,因此,他們後來的表述,主要採用法律的語言,堅守法律主義立場,對他們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當他們目擊「公民社會主義運動」被扼殺,他們曾經的同伴被判重刑,也深深感到在國內難以找到釋放的管道,於是他們的思路便轉向國際,將自己的主要目標定位為爭取西歐國家共產黨的支持,尤其是由義大利共產黨領頭和象徵的「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因此,他們也將自己視為「歐洲共產黨人」,他們的沙龍聚會也有了一個名字“E-club”。
1968年蘇軍入侵對於西歐共產黨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形成了20世紀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另一個重要轉捩點。尤其是義大利共產黨對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實驗始終表現出明顯的興趣。1973年,義共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 (Enrico Berlinguer, 1922-1984)制定了「歷史性妥協」方針,包括接受北約,支持美蘇和解,克服歐洲軍事集團的對立,與60年代末開始的國際緩和進程相一致。在國內,義共也提倡與其他政治力量團結合作,該黨1976 年6月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創下了歷史新高。1977年3月,義共、法共和西班牙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馬德里舉行會議,通過了《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又稱《馬德里宣言》,其中全面闡述了「歐洲共產主義」的基本主張,即拒絕蘇聯共產黨的影響,認為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本國的條件和需要制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前共產黨人從自身經驗中,體驗最深的也正是這一點,他們覺得與歐洲共產主義立場最為接近。
而68年流亡者中正好有這麼一位能量極大的樞紐人物,能夠在捷克境內被驅逐的黨和義大利共產黨及西方歐洲共產主義之間架設一座橋樑,讓困境中被扼殺的反對聲音在國際範圍內得以聽見。這也是一種能量傳遞——在國外發出的聲音又傳回國內,鼓舞和激發了國內的人們,包括促進原體制內與體制外人們之間的互相交流,轉而產生更大的能量。這位關鍵人物便是伊日.貝利康(Jiří Pelikán, 1923-1999)。「布拉格之春」時,貝利康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電視臺台長,他的電視臺成為人們了解這個國家改革進程各種事件的最佳視窗。蘇軍入侵之後他被派到駐義大利使館任文化參贊,從此一去不返。1971年貝利康在羅馬辦起了流亡雜誌《信報》,經過兩期試刊之後,於1971年1月作為雙月刊定期出版,其副標題便是 「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反對派雜誌」。這份雜誌視自己為一個更廣泛的抵抗或反對運動的中心,將自己定位為國內社會主義反對派的一部分,只是暫時生活在國外。本文選擇「社會主義反對派」這個名稱就是貝利康最先開始使用的。不管怎麼說,貝利康的這份雜誌,可以視為「公民社會主義運動」的國外操盤手和前改革派共產黨人的國外代言人,如果這兩批人可以加起來籠統地稱之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反對派」,那麼《信報》則像是這個左翼大團體的機關報。當然,也不止於此,哈威爾1975年寫給胡薩克總統的信,最先也是發表在這份刊物上面。1978年下半年,哈威爾已經感到員警的腳步聲再次臨近,他於11月18日寫信給已經流亡的姆林納日,希望自己的〈無權者的權力〉這篇重磅文章也能夠在這份流亡雜誌上發表。
這批被驅逐的前共產黨人政治經驗豐富,在國內外擁有享有較高聲譽,一舉一動備受關注。在貝利康的牽針引線之下,1971年斯姆爾科夫斯基率先打破沉默,接受義大利共產黨雜誌《新生活》的採訪,表達了對於蘇聯入侵最嚴厲的譴責及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現在看來這樣的做法平凡無奇,但是在當時,斯姆爾科夫斯基這樣做,相當於某位被罷黜的中共領導人,比如趙紫陽接受境外香港或美國記者的採訪,很快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當然,斯姆爾科夫斯基選擇通過義大利左派平臺發出聲音,還是有些不一樣,這個舉動可以向世人包括捷共統治者證明,他們這些人不是站到資本主義一方去反社會主義,而是仍然處於社會主義陣營當中。1974年1月斯姆爾科夫斯基去世後官方所採取的蠻橫態度,讓一直低調隱身的杜布切克坐不住了,他給逝者的遺孀寫了一封悼念信,這信經過貝利康之手也發表在同一份義大利雜誌《新生活》上面。接著,杜布切克又發布了兩份公開信,給國內的聯邦議會和西歐的共產黨領導人,前一份也發表在貝利康的雜誌上面。不管杜布切克說什麼,這是他1970年被開除黨籍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後的首次發聲,在當時仍然有著巨大能量,不過從此杜布切克又沉寂下去。
斯姆爾科夫斯基去世前,曾表達過讓姆林納日承擔起他的角色,成為這批人的召集人,姆林納日臨危受命。也因此,從1974年到1977年6月姆林納日流亡,這段時間是前共產黨人的反對活動最為活躍時期。與其他人不同,姆林納日喜歡著書立說,他以個人名義寫下大量文章,包括不止一封給歐洲共產黨的公開信等。也經歷了對於西歐「歐洲共產主義」的希望和失望。1975年初,姆林納日完成了長文——〈1968年改革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準備提交給原打算同年晚些時候舉行的「歐洲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大會」,其中全面分析了從1968年到當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勢和發展狀況,對胡薩克政權及其「正常化」政策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姆林納日把手稿複製成若干份,早早發到參加大會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手中,希望在柏林大會上引起關注,將「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作為一個議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範圍之內造成對於蘇聯的一致譴責。結果會議推遲到1976年6月才召開,並且以不討論具體國家問題的理由,拒絕了捷克斯洛伐克議題。西歐共產黨人從蘇聯獨立出來的嘗試顯示了其局限性,一些政黨在經濟上還要仰仗蘇聯的支持,這令姆林納日的幻想破滅和產生重大思想轉折。這迫使他目光向下,在共產黨之外重新尋找力量的源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1976年柏林共產黨會議後,我擔任領導職務的前KSČ(捷共)反對派團體的政治方向發生了變化。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不「自下而上」地反對胡薩克政權,我們的事業就沒有前景,因此我們尋求與其他非共產主義反對派團體的聯繫。1976年年底,調整方向的結果是創建了「七七憲章」;哈耶克代表前共產黨人團體成為其發言人。(2003,《尋找》)
姆林納日把「七七憲章」視為他們自己調整立場的一個結果,是一個集體轉向。當然,這也與他們68年試圖把黨和社會聯繫起來的努力是一致的。他們重新出發的起點是經由《赫爾辛基協議》進一步擔保的國際人權公約,核心是「人權」。在1989年東歐社會轉型研究中,始終存在著一個「赫爾辛基敘事」,即把1975年頒布的《赫爾辛基協議》視為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站,由此而撬動了後來一系列的轉變,這有相當的道理。
《赫爾辛基協議》源自蘇聯在1954年美、英、法、蘇四國外交部長柏林會議上提出的「歐洲共同安全條約」概念,其原意在確保二戰之後的蘇聯侵占的東歐領土的邊界得到國際承認,提高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合法性,削弱北約尤其是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但西方世界對這個議題長期不感興趣,直到在「國際緩和」氛圍中的1973年,才在赫爾辛基舉行第一次歐安會。在兩年的艱苦談判期間,這個活動一直受到西方精英和草根階層普遍譴責,認為這是對蘇聯極權主義及地區霸權的讓步。1975年7月,因尼克森水門事件下臺而擔任美國總統的吉羅德.福特,啟程動身前往赫爾辛基簽訂協定,《華爾街日報》7月23日社論的標題為〈傑瑞,別走〉,意思是此行凶多吉少,是幫助蘇聯從中漁利。對於兩次經歷了西方世界背叛的捷克斯洛伐克,一般人們更是有理由認為這是「新慕尼克協議」或「新雅爾達協議」,是同意和預設以蘇聯為首的華約軍隊的入侵。1975年早些時候,布拉格有社會學家就是否期待赫爾辛基會議結果進行民意調查,187位受訪者有138名直接回答「沒有期待」,甚至有人說:「我不相信西方會取得任何成果。……俄羅斯人總是會欺騙他們。西方將死於過於民主和天真。」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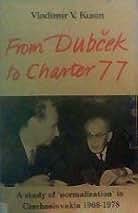
尤其是後來看到官方主流媒體上一片歡呼聲,布里茲涅夫將之視為自己外交上的重大勝利,胡薩克這邊也亦步亦趨,捷克國內的異議人士對此更加反感。有人寫道:「赫爾辛基峰會祝福了蘇聯在東歐的霸權,以換取西方國家首腦對蘇聯不干涉西方事態發展的希望」。31 但協議中的稱之為「第三籃子」關於人際交往方面的內容,比如增加家庭團聚、兩國婚姻和旅行、改善記者的工作條件、資訊的自由流通等,其深厚綿密的力量還是有人覺察到了。據說蘇聯政治局內部的意識形態強硬派以及蘇聯駐外大使在看到最終草案時,都「驚呆了」。他們擔心這相當於允許外國政府在曾經純屬內部事務問題上可能發揮作用,比如關於資訊流通和如何對待不同政見者。赫爾辛基最大的特色在於,這是一個跨國的人權網路,簽署國互相之間是可以監督的,比如一位東歐持不同政見者寫信給美國外交官,要求在即將舉行的會談中解決他的困境;或者波蘭的人權活動家向波蘭駐美國大使施壓,要求釋放一名工會組織者,這都被視為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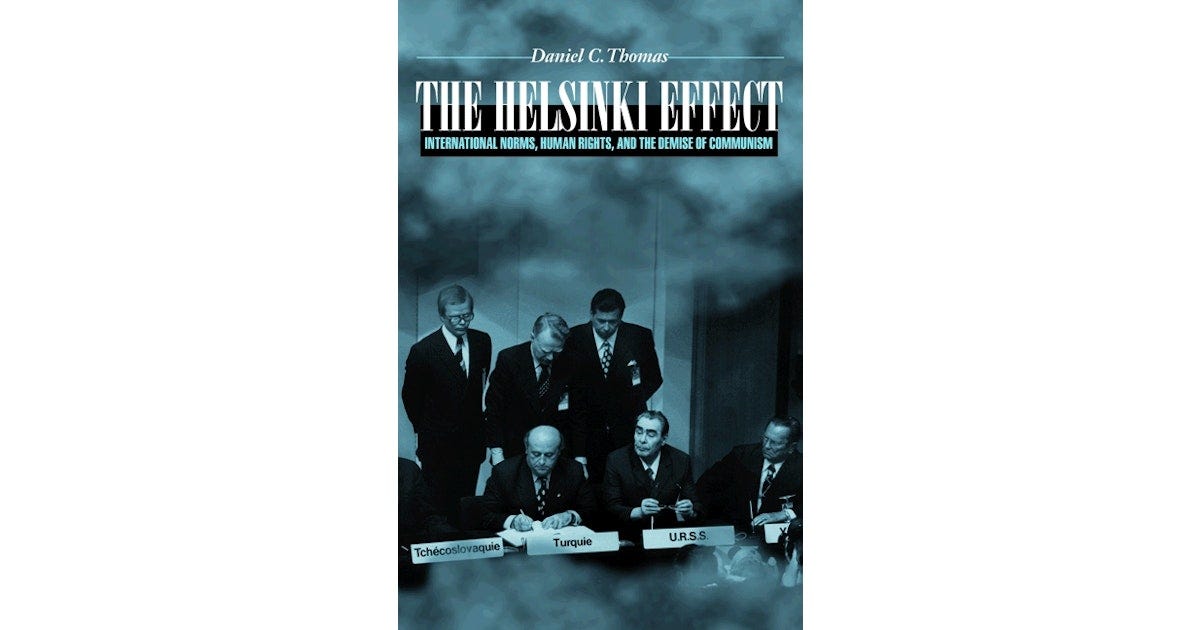
義大利共產黨和西班牙共產黨都對《赫爾辛基協議》表示了熱情歡迎。兼具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貝利康、姆林納日和哈耶克也在這個協議中,看到了國內反對者的空間。貝利康在他1976年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的書中,專門有一個章節為「反對派與國際緩和」,其中說:「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過去二十五年的歷史經驗證明,冷戰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僅沒有削弱史達林政權,反而增強了其最頑固的教條主義分子,令他們能夠為鎮壓、僵化和孤立主義政策辯護。與此相反,後來每一次緊張局勢的緩和,都帶來了壓迫和審查的放鬆,為提供更好的資訊、復甦新思想和新政治力量而創造了空間。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氛圍,『布拉格之春』的籌備和實現是不可能的。」(1976, Jiri Pelikan)換句話說,只有在寬鬆的國際環境中,才能有國內民主反對派的生存空間;而對抗緊張的國際關係,只會令專制統治者對國內反對派更加嚴厲和殘酷。
《赫爾辛基協議》發布之後的第二個月,姆林納日和哈耶克接受瑞典電視臺的採訪中,表達了三個看法,有學者認為這也是「七七憲章」背後的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1978, Vladimir V. Kusin):第一,承認每個人在自己的社會中行使個人權利,這點應該得到國家權力的尊重;第二,國際交往中通過的原則(比如人權條約),在每個參與國中具有同等效力;第三,承認存在共同的歐洲文化價值觀和人道主義傳統:「如果某些歐洲民族和國家繼續保留有悖於歐洲文明和文化基礎的內容,那就違背了赫爾辛基精神。」(2001, Daniel C. Thomas)原捷共首席歷史學家卡雷爾.卡普蘭,也於1975年10月20日致信捷共中央黨主席團、聯邦議會和聯邦政府,就赫爾辛基精神提出八項要求,包括釋放政治犯、給每個公民發放護照、停止對科研人員和學者的歧視及停止新聞審查等,逐一點出這些具體項目,也啟發和幫助形成了《七七憲章》的文本。正是此人,在1975年底,想要與姆林納日、哈耶克弄出一個類似蘇聯的赫爾辛基小組。
哈耶克顯然是共產黨反對派內部宣導赫爾辛基精神的執牛耳者。哈耶克年輕時是一名活躍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是戰後的黨內領袖人物,1948年他支持自己的政黨與共產黨合併,並擔任聯合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直到1969年被免職和被開除出黨。作為一名外交家,他始終關注戰後出現的「國際人權」概念。人們喜歡引用他說的:「我們依靠法律前進,正如《聖經》所說:『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1978, Vladimir V. Kusin)除了與姆林納日一起上瑞典電視臺,1975年10月1日,哈耶克自己又單獨給政府總理寫信,信中引用了政府1975年8月8日發表的公開聲明中承諾將始終遵守赫爾辛基文件中的條款,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所有機構都有義務,確保自1968年以來那些因不同觀點而被剝奪與其資格相符工作人們的權利,包括其子女都不應被剝奪其在藝術、科學、技術發展、經濟組織、醫療保健和文化生活中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機會。同時,任何人都不應因為反對這種歧視或傳播反對歧視的觀點而被起訴和監禁,如果他們因此而被起訴和監禁,這種迫害和歧視行為應予以制止,防止其繼續,並彌補其造成的損失」。(1978, Vladimir V. Kusin)繼而哈耶克又給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寫信,信中提到如何運用赫爾辛基條款來重新看待「布拉格之春」被鎮壓,提出必須保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和民主。
1988年11月,哈耶克創辦「捷克斯洛伐克赫爾辛基小組」,與巴泰克、烏爾的團體一道,成為組建「公民論壇」的獨立團體之一。新發現的資料顯示,哈耶克本人也是《七七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寫這篇文章快要寫完時,筆者又讀到一篇採訪。哈威爾圖書館館長馬丁.帕洛斯2017年在回答記者誰起草《七七憲章》時,稱伊日.哈耶克肯定寫了其中的一部分,「所有這些關於國際法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義務的論點,我想都是出自他之手」。32
捷克斯洛伐克前共產黨人對於《赫爾辛基協議》和人權問題的高度敏感,以及由此而確定他們自身反對道路的新策略,與他們的政治經驗和眼光,亦即政治上的成熟密切相關,許多人因此而行動起來。1975年10月,蘇聯著名的人權運動家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柯里格醫生公開表示歡迎,這無疑被視為對於官方的挑戰行為。接下來,他又聯合一起抵制《莫斯科協議》的年長聯邦議會議員蘭蒂謝克.沃德斯洛和格特魯達.塞卡尼諾娃.查克托娃,三人連署給聯邦議會寫信,要求通過1968年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關於政治權利和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與哈耶克呼應,他們也提出根據赫爾辛基精神,聯邦議會應與蘇聯就撤出蘇聯軍隊的問題展開討論。關於國內的人權問題,三位資深共產黨人呼籲釋放所有政治犯並為其恢復名譽,立即停止政治鎮壓及傷害。隨後,在赫爾辛基協議加持下的這兩個人權公約,被編在10月13日的官方法律刊物《法律彙編》中公布,在1975年11月11日獲得聯邦議會批准之後,隨即印成小冊子送達街頭報刊亭,海內達克提醒哈威爾「以不久前頒布的人權條約為基礎」,指的就是這件事。
1976年1月20日,包括柯里格醫生、哈耶克、姆林納日在內的前十四名前中央委員寫信給聯邦議會,要求釋放在押的政治犯胡布林、薩巴塔及其他人。信中稱,這些人之所以被捕,是因為他們公開宣稱有必要將社會主義與政治民主相結合,而他們的立場實際上十分接近法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官方綱領性聲明。的確,政治民主及公民權利,是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和實踐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捷共官方至少在檯面上與這些西方共產黨的保持一致,這封信把人權納入到政治框架裡,視人權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1978, Vladimir V. Kusin)。
1976年11月6日,距離「七七憲章」第一次會議僅一個月零四天,姆林納日聯合其他九名法律專家,連署了一份〈十位律師就被判刑的年輕音樂人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憲法機構的公開信〉。此時對於搖滾音樂人的審判已經有了結果,對他們的起訴書和判決書都已公開,這十位法律人針對已經公布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對年輕人提出的「罪名」和「罪證」,從法律專業的角度進行了逐一批駁。比如針對官方檔中稱年輕人是「頹廢」和「虛無主義」,這些法律人稱這些並不是刑事訴訟的主題。公開信還細數了審判過程中法庭本身違反司法獨立和公正的惡劣做法。簽署者中大都是1969年之前重量級的法律人士,比如聯邦議會憲法委員會主席、國家總檢察長辦公室重審部主任、大學法學院院長等。文中他們是這樣自我表述的:
我們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代律師,有過20世紀50年代審判和20世紀60年代強權審判的慘痛教訓,深刻認識到,嚴重違反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一再發生,特別是在刑事處罰領域,破壞了我們公民與社會主義機構的關係,並剝奪了他們對與社會主義世界觀相關的人道思想的信任。……1968年1月後,我們中的一些人有機會參與了捷共《行動綱領》的制定,其中在政治意義上規定了社會主義合法性、充分尊重個人權利和公民自由的許多保障。我們這樣做的信念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不僅允許傳統民主權利的全面恢復,而且還在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層次上確保這些權利。
這一系列產生於前共產黨人之手的文件,與後來的《七七憲章》思路完全相同,即運用現有法律來對照現實,伸張個人權利,為受不公正對待的人們呼籲。實際上,當這些前共產黨人採納「人權」的思路,是做出某些讓步和犧牲的。第一,向西方讓步。那個年代的共產黨一直自視為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橋頭堡,對來自西方陣營及帶有西方標籤的東西保持批判和警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人權」則被主要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語言。第二,向本國政府讓步。先是莫斯科定下他們外交勝利的調子,胡薩克又把不打算認真執行的國際人權公約印成小冊子送上了大街,但這些遭到排擠、被打入冷宮的前改革派沒有採取「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立場,沒有覺得凡是自己不在其中的必定是壞事,而是對這些「官方文件」採納了正面肯定的態度。第三,向他們自身的社會主義立場讓步。顯然,「人權」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可以吸納和釋放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派別及宗教,因此也能夠觸及每一個人,給全社會提供支援。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哈耶克、姆林納日這些共產黨反對派奠定了以人權為導向、以法律作為武器的反對派策略,這項策略(法律行動主義)既與廣大社會相聯繫,又提供了不同立場反對派的聯結點,也令捷共當權者啞口無言。如果說,68年之後,這些前共產黨人第一次撤退至「社會主義」,那麼,他們第二次則撤退到「普世人權」。自從70年代中期突出「人權」的主題,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中的社會主義立場的聲音實際上遭到稀釋和淡化,在一般人們中的影響慢慢減弱和邊緣化。因此,這些共產黨反對派走的是一條可以稱之為「以自身的撤退推動社會進步」的路線。
順便地說,中文世界許多人認為美國的雷根總統,在結束蘇式共產主義專制中功勞首屈一指,但真正開闢航道的,是美國的卡特總統。在他任期的1977年1月到1981年1月,正是人權運動奠定基礎和最初發揮作用時期,是卡特認真履行赫爾辛基精神,促進在蘇聯、東歐國家進行社會內部的民主「深耕」,從而幫助促進了公民運動的興起。因此,有「卡特的人權運動」之說。而以「人權」作為規範,作為與共產國家打交道的方式,實際上也避免了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直接衝突,緩和了東西方的緊張局勢,促進了東西方真正富有意義的包括民間交流。1989年在位的雷根,他早些時候對於需要花更大力氣和耐心的人權運動恰恰不感興趣。在很大程度上,與戈巴契夫一樣,這位卡特先生也是上個世紀偉大而深受低估的政治家。此處按下不表。
因積極參與創建「七七憲章」,姆林納日受到官方更加嚴密的監視,尤其是在報紙上的公開造謠侮辱,忍無可忍之下,姆林納日選擇流亡。起初他想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後來不得已匆匆去了奧地利,他臨走前還寫了一篇文章〈捷克斯洛伐克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的條件和可預見的前景(原則)〉,其中提出這些人的真正出路——「有必要將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堅定地納入『自下而上對制度施加壓力的一般民主潮流當中去。為了實現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必須 』把重點放在制度的民主化上。」(2003,《尋找》)這番話他的前同僚們聽進去了多少,很難說。姆林納日走後,他在共產黨反對派中的帶頭角色就由米洛什.哈耶克來擔任,這是不同於前外交部長的另一位哈耶克。
米洛什.哈耶克(Miloš Hájek, 1921-2016),歷史學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社會主義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對象為捷克近、現代史,包括捷克土地、國際勞工、民族問題等。納粹占領期間他成為堅定的共產黨員,曾因參加地下抵抗運動,被蓋世太保監獄判處死刑,斯姆爾科夫斯基領導的五月起義將他解放。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即使在60年代政治寬鬆時期,他也因其修正主義歷史觀被大學革除。68年復出,是維索卡尼黨代表大會的組織者之一,《七七憲章》第一批簽署者。正好是1988年,米洛什成為前共產黨人的憲章發言人,因此這個時期憲章的相對保守面貌受此人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後加入憲章的年輕人感到不滿也與此有關。
米洛什主持下的E-club,是憲章內最低調沉默的一群。這些人仍然在期待現有體制內部改革的可能性,避免與執政的胡薩克集團發生正面對撞,因此在某些事情上與其他憲章成員有分歧。比如對待波蘭「團結工會」的態度,官方跟隨蘇聯陣營一致予以譴責,這些前共產黨員也就比較猶豫,怯於公開表態支持。到了1985年戈巴契夫上臺,1987年他逐漸清晰的「新思維」——除了經濟改革,還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領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提倡尊重人權、公開性和多元化,建設人道的和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才重新點燃了這批捷克斯洛伐克前改革的共產黨人的希望,他們從中看到的是自身在68年被鎮壓的理想,只是相差了20年。
1987年,「七七憲章」內的這些前共產黨人給戈巴契夫寫了一封信,稱他為「同志」,這引起了烏爾、哈威爾等人的不滿及擔憂。隨著戈巴契夫改革的深入,E-club人們的社會主義熱情及相關討論越來越高漲,漸漸形成一支與「七七憲章」相平行的政治力量。他們視自己的使命為修復社會主義制度,實際做法則傾向於與共產黨進行溝通,而不是通過公眾對權力施加壓力。一些沒有簽署《七七憲章》的前改革派加入到他們當中去,比如切斯米爾.西薩(Čestmír Císař, 1920-2013),他也是「社會主義復興聯盟」(Obroda)主要創辦人。這位西薩聲望很高,曾經做過教育和文化部長(1963- 1965),一度擔任國民議會主席(1969-1970),1970年被開除黨籍,1988年他在流亡雜誌《信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戈巴契夫的計畫和68年捷共《行動綱領》之間的密切聯繫,他呼籲需要實施一個真正的改革主義政策,能夠吸收和處理來自公眾輿論的能量。他認為「七七憲章」已經變成一個脫離社會的自我隔離的區域,呼籲他的同志們離開而重啟與政府之間的建設性對話。總之,這個社會主義再次復興項目,雖然將「多元化」放到了重要位置,但是骨子裡還希望有一次「從上到下」的改革,當然是由共產黨來主導,只不過不是現在這個統治成員的班子。
1989年12月份,這位西薩與杜布切克都出現在總統競選候選人的名單上,當然杜布切克比西薩要強勢得多,一度姆林納日也在前共產黨人候選人的名單上。哈威爾與杜布切克和西薩都進行了單獨交流,與杜布切克談了五次,針對如何讓自己領先與他們進行了具體談判。哈威爾也禮節性地見了11月底從奧地利匆匆趕回去的姆林納日,但沒有展開交談,姆林納日感到自己被冒犯了。
1989年11月24日傍晚,哈威爾和杜布切克同時出現在布拉格梅蘭特里奇大樓的陽臺上面對公眾,這時傳來捷共中央總書記米洛什.傑克斯(Miloš Jakeš)和他的領導層辭職的消息,於是這個國家未來總統的真正競爭便在這兩人之間展開,擁有1200名成員的「社會主義復興聯盟」是杜布切克的堅定後方。12月初「公民論壇」有一份對於布拉格民眾的民意調查表明,杜布切克受歡迎的程度為11%,哈威爾為1% (2009,Daniel Kaiser)。三個星期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議會選舉杜布切克為聯邦議會主席;第二天即1989年12月29日,由該聯邦議會全票選出哈威爾擔任總統。
小說家伊凡.克利瑪解釋過這個戲劇性的轉變。1989年11月底某日,他與一些朋友們從「公民論壇」回來,說起提名總統候選人的事情,「他們都同意考慮的唯一候選人是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幾個月後,在面對美國小說家羅斯的問題——哈威爾「並不是你們當中唯一頑強的和善於雄辯的,也不是唯一因思想而坐牢的」,那麼,這種大運是怎麼讓哈威爾撞上的?克利瑪的回答是,任何與前共產黨政權有牽連的人,都不被捷克青年人所接受。當然更重要的,「大多數人恨這個前制度,因為它以可怕的方式令人們與其共謀,讓人們感到自己遭到欺騙和羞辱。」33
羅馬的流亡雜誌《信報》上發表了上述幾乎所有這些左翼反對派的重磅文章及討論,在不同圈子的國內人們之間及國內外的互動傳遞中,產生了巨大的反對能量。姆林納日流亡之後,很快也加入到貝利康的團隊,成為《信報》的一名編輯。
這位貝利康之所以有著如此強大的行動能力和活動能量,與他50年代擔任「國際學生聯合會」(IUS)主席有關,這期間他結下了廣泛的人脈。1969年貝利康流亡義大利之後,立即參與當地政治,1977 年獲義大利公民身分,並從1979、1984 年連續兩屆擔任義大利社會黨歐洲議會議員。他本人和他的團隊與西歐左派最高政治代表建立了聯繫,比如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國家總理貝蒂諾.克拉西(Benedetto Craxi)、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1986年被刺殺)、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Bruno Kreisky)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貝利康的神通廣大,為他的雜誌找到了足夠的資金來源。這位貝利康先後四次來到中國,見到過從毛澤東到胡耀邦等中共領導人。
以「國際學聯」領導人的身分,1956年貝利康第一次來到中國,正逢中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討論非常熱烈,有人告訴他想請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教授來北京、上海教學,令他感到耳目一新。不過當他聽到中國人說「覺得戰爭沒有什麼可怕,在戰爭中帝國主義會毀滅,人類社會一定會進步」,這讓他覺得有點玩世不恭。他第二次來中國是在1959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典禮,他們一行人在中國先是轉了一個月。在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他看到了數以千計爐火通紅的小高爐,不過在中國工作的捷克技術人員告訴他,這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貝利康聽說中國高校把學制從五年改成三年,有學生自己編寫新的革命教材,還是超出了他的理解力。10月1日他上了天安門城樓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走過來,與他握手之後說了幾句中文,無奈貝利康的翻譯無法現場應付毛澤東脫口而出的中國古代詩歌。他承認中國許多事情讓他迷惑,他經常向人們發問的是,為什麼毛澤東不向黨員、黨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直接發表講話?沒有人能夠回答他的問題。但是中國想要走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並且抱有某種好感和期待。也是在這個期間,他結識了時任共青團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和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的胡啟立。後者還擔任過貝利康位於布拉格的「國際學聯」這個組織的書記處書記和副主席。1958年,貝利康與這兩位中國青年運動領導人就南斯拉夫學生來中國參加活動的簽證通過信,雙方留下了個人印象並結下友誼。50年代的貝利康,還結識了當時在「世界青聯」工作的吳學謙(1978年的外交部副部長及部長)和錢李仁(第二任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1989年期間的《人民日報》總編)。
毋庸置疑,中國是譴責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為嚴厲的國家,這讓貝利康產生了良好印象。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貝利康請他在紐約的流亡者朋友,遞給駐聯合國的中國使團一封信,信中表達了他希望向中國官員通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和當地社會主義反對派運動的情況。有意思的是,這位流亡中的貝利康,從來也不以被驅逐者自居,而是把自己認作了正統捷共中央代表,信中自詡為「1968 年當選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代表小組」和「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社會主義運動」,信的末尾,他署上了自己「捷共中央委員」的身分。1973年起,貝利康便與中國駐羅馬的大使館保持定期聯繫,將自己的雜誌送給他們。據貝利康的日記記載,中國人對該雜誌的捷克語和義大利語版本都表示了濃厚的興趣,1974年開始正常訂閱並提供資金支援。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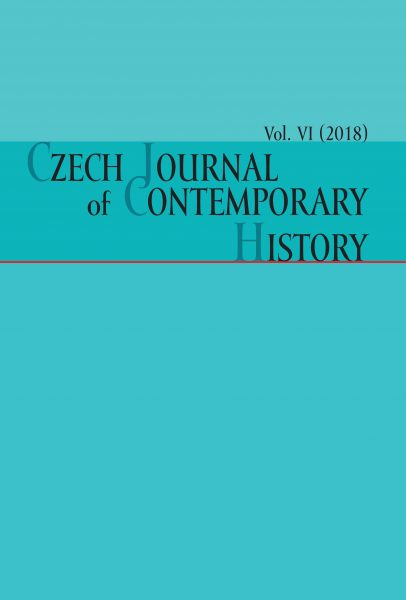
當時有一些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激進學生和科學家,反蘇或者反蘇也反美,他們試圖與中國建立聯繫,中國使館也與他們個人進行接觸,免費讓他們來中國參觀。貝利康找到了他們,將他們納為他雜誌團隊的成員,這些人回來寫的中國觀感也發表在他的刊物上面。一名學生叫做卡雷爾.科萬達(Karel Kovanda, 1944-)68年時是年輕的學生領袖之一,1970年去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政治學,始終在關注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和中美關係,他與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的大使館取得了聯繫。麻省理工學院也有一個蘇聯研究系,科萬達可以接觸到一些與蘇聯有關的材料,如大赦國際的文件和俄羅斯地下雜誌《當代紀事》,中國外交官對這些很感興趣。1972年中國邀請了這位年輕人訪華。1976年中國考慮邀請一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捷克文專家,想在捷克境內的持異議者中尋找,顯然這不現實,於是向貝利康團隊發出了邀請。1977年夏天年輕人科萬達作為捷克文專家走馬上任,在他動身去中國之前,貝利康和姆林納日會見了他,兩人向年輕人面授機宜,此時姆林納日剛流亡不久。作為中國電臺顧問,科萬達也始終與這二位保持聯繫。科萬達很快發現,中國只報導來自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發布的消息,而不會報導任何反對派的活動。他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飆寫過一封信,建議在蘇軍入侵日和柯里格醫生生日紀念日可以做點什麼,但是石沉大海。兩年之後,科萬達的接班人也是貝利康挑選出來的,是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
經過了包括駐義大利使館在內的多位中間人,再加上50年代的交往,中國方面對貝利康瞭若指掌。1979年11月貝利康本人終於再次來到中國,他是以歐洲議會議員的身分,這邊則是中共中央的正式邀請,接待他的規格屬於社會主義兄弟黨的水準。對外聯絡部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吳學謙(也是他的老朋友)會見了他,尤其是已經復出的胡耀邦(時任中宣部部長、政治局委員)在平反冤假錯案的百忙中,也抽出時間與貝利康見面,全國青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胡啟立也一併在場。貝利康稱,在與這些中國高級領導人的會面中,他們對歐洲議會的運作、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現狀均表示關注,而且也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布拉格之春」,特別對經濟改革的工作(計畫與市場的關係、引入私營部門)感興趣,非常歡迎有關「布拉格之春」經驗的議題,並對「七七憲章」、「保衛受不公正起訴的人的委員會」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資訊也想了解。貝利康感受到中國試圖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及急切想要進行經濟改革的嘗試。貝利康告訴中國同志,他的雜誌不是非法組織,而是願意向國內同胞和全世界公開自己的一切活動。貝利康也讓他雜誌的同伴知道,中國同志對他說,知道你們工作條件很困難,我們想提供3萬美金聊表支援。貝利康在個人日記中寫道,「他們每個人都聽美國之音」。(2018, Petr Orság)
儘管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但貝利康被告知,中國政治家希望這是一次友好的訪問,而不是正式的訪問,因此對新聞界和公眾保密。結果,中國媒體對此一字不提,西方一些媒體作了報導,比如義大利的《晚郵報》、法國的《世界報》。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報紙對貝利康此行做了污蔑性的報導,稱邀請這位「叛徒」是「反捷的姿態和挑釁」。莫斯科的《真理報》也發表了同樣口吻的文章,很快被全文翻譯登在捷共《紅色權利報》上。中國方面當然會關心這次訪問的反應,但看上去貝利康與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受到影響。因為貝利康的推薦,姆林納日這本關於「布拉格之春」最為生動和權威的書《嚴寒來自克林姆林宮》(1978),於1980年4月由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與英譯本同年面世,此前我還一直暗嘆當時中國捷克文專家如此敏感和敬業呢。1983年,貝利康自己關於68年的回憶錄《永無盡頭的春天》也在中國出版,北京出版社,書的副標題為「一個布拉格共產黨員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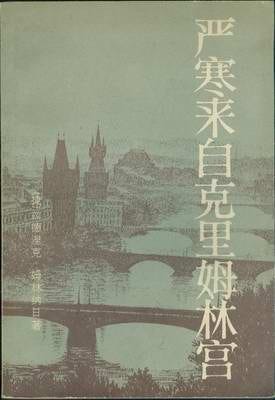
令人訝異的還有,1981年春,貝利康以他的雜誌團隊的名義,組織了四位流亡者來到中國,其中就有姆林納日。據說此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其間所有的旅行、考察、住宿一切費用由中方承擔。目前僅能看到他們一行人在故宮、長城遊覽的照片,關於他們見了什麼人,談了什麼問題,尚有待了解。中共在外交上一向謹慎,當然事先知道這些人有家不能回的「敏感」身分。而此時,哈威爾正在為他最長的那次四年半的刑期坐牢。這一行人回去之後,再加上學生科萬達和一位元核子物理學家弗朗齊謝克.雅努什 (František Janouch,1978年底他在斯德哥爾摩創辦了《七七憲章》基金會),他們分別寫了關於中國的觀感收在同一本文集裡面《我們眼中的中國》,1982年由流亡出版社Index出版。貝利康和姆林納日最終都發現,即使中共強烈譴責蘇軍入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民主化。對於中國人剛剛掛在嘴邊的改革開放,他們也認為無法與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改革相提並論,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有自己的民主傳統。
這本書裡還有一位作者——經濟學家伊日.科斯塔(Jiří Kosta, 1921-2015)。也是因為貝利康的推薦,科斯塔的這本《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於1981年由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布拉格之春」時,這位科斯塔擔任副總理、經濟改革之父奧塔.希克的助手。科斯塔流亡之後在法蘭克福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出於個人專業的原因,他始終對中國經濟感興趣,他聯繫了中國駐波恩大使館,1974年他加入了一個團隊訪問中國。貝利康給他提供的資訊和人脈,使得科斯塔能夠突破一般旅行團的框架。在上海,科斯塔能夠與幾位經濟學者進行交流,釋放他關於國家經濟轉型的興趣。貝利康提醒他,不同於蘇聯,中國經歷過並實行經濟與行政權力的下放。由此也可見,貝利康對中國是下了一些研究功夫的。
奧塔.希克本人於1981年春天也來到了中國。他1968年移居瑞士,較早成為貝利康雜誌的核心成員,但因為更願意聯合無黨派人士一道工作,不久之後與《信報》分道揚鑣。1981年3月到4月,希克應邀在北京、上海、蘇州三個城市做了七場學術報告,參加座談會。他建議經濟改革可以從價格入手,先建立自由價格制度,用市場價格體系來代替計畫價格,這是一個可以著手的具體問題,「姓社姓資」的尖銳性被暫時放在了一邊。他沿途作報告時,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全程陪同,並把希克報告的內容做成簡報及時上報給社科院領導,簡報也及時抵達了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案頭。趙紫陽為希克特地做過指示——聘請希克為社科院顧問;每年要請希克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希克給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一個直接結果是建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1982年,中國出版了希克的三本書《第三條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現代工業社會》(人民出版社)、《社會主義的計畫與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共產主義政權體系》(江蘇人民出版社)。然而,中國的改革總是走走停停。1982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的文件指希克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實際上比較起當時請來的各路專家,希克的理論最接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之後希克沒有能夠再來中國。第二年,他當年的年輕助手科斯塔來到中國,與其他來自波蘭、西德的專家一起出席了「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科斯塔的發言為「工資、獎勵和收入分配上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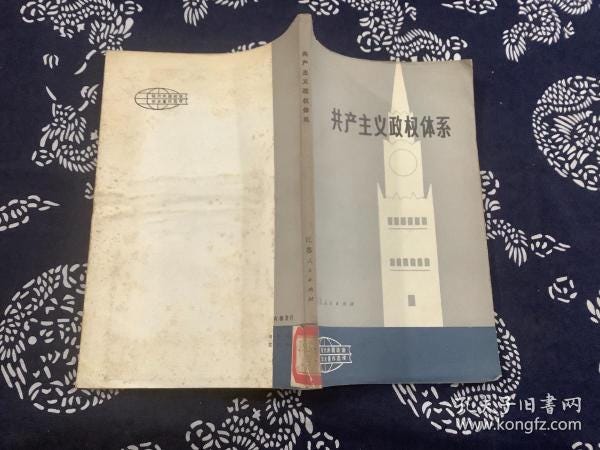

令人浮想聯翩的是,1981年這個百花齊放的春天,即希克抵達北京的時間,與姆林納日一行四人在中國的時間大致重合。不知道這兩位「布拉格之春」民主社會主義實驗中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設計師,在離開他們的祖國若干年之後,有沒有在北京見上一面?如果見面,他們會產生什麼樣感想和展望?當然,這是一個關於當時中國往何處去的一個想像。1981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一書,運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提出的人及人的異化問題,試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人性面貌,以此來推動中國現實中的政治民主的改革。這種努力與當年「布拉格之春」之間存在一個平行關係,都是期待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和社會主義制度內部開啟一個復興進程。
1983年貝利康作為歐洲議會議員隨同歐洲議會代表團再次訪華。他回去向歐洲議會轉達了有關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變化的情況報告,特別提出了發展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經濟合作的倡議,指出中國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作用日益增強,提到那裡有 10 億人口的中國市場。這一次他又見到了他的老朋友胡耀邦,應該是一次非正式的私下宴請,此時胡耀邦已經是中共中央總書記。
1989年12月貝利康帶著他的雜誌回到他的祖國,他拿掉了雜誌副標題中「社會主義反對派」這個字眼,代之以「獨立」二字,更新了他的編輯部。在一封給合作者的信中,貝利康寫道,「眼下在布拉格盛行的氣氛是,歇斯底里地反共,而且更多的是針對68年(被罷黜的)的前共產黨人,而不是針對雅克什和比拉克。」35(2018, Petr Orság)1990年之後,貝利康和希克都曾短暫擔任過哈威爾政府的顧問。
1991年2月,根據當時的一項「威脅和平法」,姆林納日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原因是他在1968年期間,試圖組織親蘇的工農聯盟政府,由於20年的時效已過,起訴被中止。1995年又重新啟動了該案件,結論與此前同。涉事過程在姆林納日那本《嚴寒來自克林姆林宮》一書中有所交代,關於他與蘇聯大使斯捷潘.契爾沃年科之間的一場談判,事件本身並不是什麼新聞。從一個法治的提倡者到被起訴者,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對姆林納日是一個沉重打擊,由此基本上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姆林納日於1992年出版了他自己的文集,其中收入他1975年到1989年間的主要文章,這個時間段涵蓋了他整個反對派的生涯,書名為《一個自由職業的社會主義者》。
崔衛平,自由學者,現居香港。關心東歐反對派議題。近年來有Samizdat譯著《平行城邦》(2023)、《希望與絕望》(上、下,2025)、《尋找失去的意義》(上、下,2025)。
本文注釋:
1 Alessandro Catalano “Zdeněk Mlynář and the Search for Socialist Opposition From an Active Politician to a Dissident to Editorial Work in Exile,” Cze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II / 2015, 90-156(以下簡稱〈尋找〉). https://www.usd.cas.cz/casopis/czech-journal-of- contemporary-history-3-2015/
2 中文版《哈韋爾自傳》,李義庚、周荔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3月)。
3 《哈韋爾自傳》,頁121。該書譯者將此人譯為茲登涅克.姆林納什,本文從譯自捷克文的《嚴寒來自克里姆林宮》,一律譯作茲德涅克.姆林納日。
4 Michael Zantovsky, Havel: A Life, Grove Press, New York, 2014, 170.
5 Jonathan Bolton, Worlds of Dissent, Charter 77,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and Czech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4.
6 Daniel Kaiser, Disident: Václav Havel: 1936-1989, Ladislav Horáček – Paseka 2009, 118.
7 Jiri Hajek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Vaclav Havel, John Keane, Routledge, 1985, 134-140.
8 1976年9月創立,被認為是波蘭乃至東歐的第一個反對派民間組織,最初旨在為當年在拉多姆和華沙的抗議遭到報復而被捕的囚犯及家人提供法律和經濟援助,其成員先後遭到官方各種報復,但他們的努力和犧牲也在第二年春天得到了回報——官方被迫大赦罷工的監禁者,該組織也由此更名為「社會自衛委員會」。
9 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On Perestroika, the Prague Spring, and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ism, by Mikhail Gorbachev, Zdenek Mlynár, Translated by George Shriver, New York and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
10 除了〈尋找〉作者、義大利歷史學家Alessandro Catalano(1970-)外,捷克當代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日.蘇克(Jiří Suk, 1966-)2003年出版的《革命的迷宮》以及他2023年與人合作出版《歷史沒有為我們所終結——捷克左翼流亡者的政治工作和思想》(1968- 1989),查理大學歷史系教授米哈爾.科佩切科(Michal Kopeček, 1974-)2019年出版的《尋找失去的革命的意義》,以及科佩切科的學生克莉絲蒂娜.安德洛娃(Kristina Andělová, 1987- )2021年的博士論文《1968-1990年捷克改革共產主義思想史》,都頻頻提及姆林納日。
11 Adam Michnik, “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Tradition: Imprisonment or Lib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2, No. 4; Elzbieta Matynia, “Introduction: 1989 and Beyond: The Futur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I). ” (Dec, 2009), pp. 445-452.
12 奧塔.希克,《第三條道路》,〈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7-8。
13 《哈威爾文集》,崔衛平譯,Samizdat,2003,頁39。
14 Ladislav Hejdánek,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n,” Vaclav Havel, John Keane, Routledge, 1985, 144.
15 Vladimir V. Kusin, “Challenge to Normalcy: Political Opposition inCzechoslovakia, 1968-1977,” In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Edited by Rudolf L. Tokes, London: MacMillan, 1979, 46.
16 胡塞爾曾將馬薩里克稱作「我的第一個老師,是第一個在我心中喚起了對世界與生活的倫理理解的人」。見倪梁康,〈胡塞爾與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作為實踐哲學家的現象學家〉,《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17 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Otázka sociální – základy marxismu sociologické a filosofické – 1. VYDÁNÍ: Část druhá – základy marxismu sociologické a filosofické, Omas Garrigue Masaryk,〈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和哲學基礎〉,第1版,第二部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和哲學基礎》,Praha, 2017, 19-20。
18 Karel Capek, Talks with T. G. Masaryk, Michael Henry Heim (Translator), Catbird press, 1995, 122.
19 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1945-2005》,林驤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頁183。
20 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2002, 61.
21 Arckie Brown, “Introduction” In 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2002, xi.
22 Tina Rosenberg, The haunted land: Facing Europe’s Ghosts After Communism, Vintage, 2012, 50.
23 R. J. Crampton,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nd After,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1997, 340.
24 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1945-2005》,林驤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頁610。
25 Václav Havel, “On the Theme of an Opposition,” In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Vintage, 27.
26 《哈威爾文集》,Samizdat ,頁184。
27 Rudolf L. Tokes,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79, 63.
28 Jiri Pelikan, Socialist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zechoslovak Example, Palgrave Macmillan, 1976, 125-134.
29 《參考消息》,1978年4月11日,〈外電報導薩巴塔接任捷「七七憲章」運動發言人〉。
30 Vladimir V. Kusin, From Dubcek to Charter 77: A Study of ‘Norm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 1968-1978,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292.
31 Daniel C. Thomas,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96.
32 生於1950年的馬丁.帕洛斯(Martin Palouš),也是《七七憲章》首批簽署者,翻譯過漢娜.阿倫特著作。「天鵝絨革命」後曾任捷克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捷克駐聯合國大使。
33 伊凡.克利瑪,《布拉格精神》,保羅.威爾遜英譯,崔衛平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6),頁94。
34 Petr Orság,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against the Czechoslovak ‘Normalization’ Regime Exile Listy Group and Its Search for Political Allies, against Soviet Power Domination in Central Europe,” Cze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I / 2018, 62-99.
35 米洛什.雅克什(Milouš Jakeš, 1922-2020),1987-1989年擔任捷共總書記;瓦西爾.比拉克(Vasiľ Biľak, 1917-),捷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
由于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民主季刊》资金来源变得不稳定。如果您认同季刊的价值,请打赏、支持。当然,您可以点击“稍后再说”,而直接阅读或下载。谢谢您,亲爱的读者。